原文:Can you give my son a job?
来源:伦敦书评
作者:Slavoj Žižek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21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一位台湾网友的初译,如需署名,请联络
本书信息:
书名:《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作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出版社:Harper
页数:302页
定价:$27.99. Allen Lane; £25.
亚马逊地址:Amazon.com, Amazon.co.uk
传记作家威廉姆·陶伯曼(William Taubman)将赫鲁晓夫于1956年谴责斯大林罪行的讲话,评为“使苏维埃政权和他自己落入永无翻身之境”的政治行动。虽然这种判断为纯粹投机之举,但这一讲话的还不止如此,这不仅仅是某种难以从政治策略上合理解释的过份鲁莽。这一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有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因赫鲁晓夫的讲话而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我想说的重点不是要指出这些死者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当中有大多数都是对苏维埃不抱幻想的残忍的操控者。他们之所以倒下,全是因为那个作为支撑着他们持续无情及权力之争的“大他者”(Big Other)1的“客观”幻象瓦解了。一直以来,他们都躲在这个“大他者”的后面,凭藉它来代表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但现在这个替代品四分五裂了。
赫鲁晓夫在赌一把,试着以他(有限)的忏悔来壮大共产主义运动,结果在一段短时间内他成功了:我们应该始终记住,赫鲁晓夫年代是怀抱着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真诚的共产主义狂热的最后阶段。当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时,曾对当时的农业部长说,“你的孙儿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中”。他当时是代表全体苏维埃的政治精英做此论断。故此,即使到了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的时候,当他也希望对过去进行更激进的指责时(包括布哈林时期有所恢复),但结果列宁还是无懈可击的,托洛斯基仍然非同凡人。
以上述事件与毛时代之后的中国作一比较,正如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党》(The Party)中所表达的:邓小平的“改革”走向了天差地别的另一方向。在经济组织上(以至文化上),通常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被摈弃,通向西方的大门被称为“解放”:私人产业、追求利润、享乐式个人主义的生活模式等等。中国共产党虽继续维持着领导权,但已不是基于正统的教义(官方的论述中,和谐社会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取代了所有共产主义的成份),而是这样的理念:确保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才是中国稳定和繁荣的唯一保证。
中国共产党要维持其领导权,其中一个主要的手段便是严密监控及规定如何讲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过去二百年的历史。这种中国的屈辱历史故事不停地在国家媒体及教科书中反复出现,从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的胜利结束。要爱国,就要拥护共产党的统治。当历史被用于维护政权合法性时,它便不能支持任何实质性的自我批判。中国从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中学到了教训,这就是“全面承认‘原罪’(founding crimes)2会导致整个体系土崩瓦解”。换言之,他们必须抵赖!不错,某些毛泽东的“过份”和“错误”是被谴责了(大跃进和接着蔓延开的饥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七分功三分过”的评价被收录到官方记述中。然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了正式结论,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与深化都变成多余。毛泽东或许是有三分错,但他仍然被当作是“建国之父”。他的遗体在水晶棺中,他的肖像也在每张钞票上历历可见。如果破除对他的神话迷信的话,每个人都知道毛泽东做了错事,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他的光辉形象仍然神奇地毫发无损。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就一举两得了:经济上的解放与党的持续统治完美结合了起来。
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党的统治是如何与现代国家机器相结合,规范爆炸性增长的市场经济?什么形式的制度现状在支撑着官方的说法:股票市场上表现良好(投资获得高回报)成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不仅仅是私有化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政治权力的联姻。国家和党坐拥主要的中国公司,特别是那些大企业,正是党自己要求这些大公司在市场上表现良好。要解决这个明显的矛盾,邓小平调配出独特的双规制。“作为组织,党既在法律之外,又在法律之上。”北京大学的法律教授贺卫方向马利德说:“它应该有个合法身份,也就是说,是个可以被起诉的法人,但它甚至没有注册为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完全存在在法律体系之外。’”马利德写道:
“要将一个大得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隐藏起来,但同时又让它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似乎是件困难的事。大型的党组织控制着人事和传媒,它们在公共场合刻意保持着低调。而党委(即“小规模领导集团”)指导并独断地决定各部门的政策,这一切都在暗中进行。所有的委员会的构成,甚至它们的存在本身,在国营媒体上都极少被提及,更不要说决定是如何达成的讨论过程了。”
但发生在邓小平年代的一则轶事正好反映出党组织的奇异之处。当邓小平还在世时,他已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那时一位政治精英中的高层人物3被清洗。遭到清洗的正式原因就是他在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时泄露了重大的国家机密:邓小平仍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他在拍板做所有的决定。事实上,所有人都对邓小平仍在幕后操纵心知肚明;但是这是不允许被正式提及的。所以,这个秘密已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秘密了:它宣布自己就是那个“秘密”,如同国王宣布自己穿着“新衣”。4因此,今天人民不应该不知道是这个秘密的党组织在管理者国家机构,而是大家都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秘密网络的存在和能力。
政府与其他的国家机关“在表面上显得它们和在别的国家一样行事”,正如财政部制定预算,法庭认定罪犯,大学授业和颁发学位、神父主持宗教礼仪,它们都在明处活动。所以,一方面我们有法律体系、政府、民选的国民议会5、司法机关、法治等等。但在另一方面,官方所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法却说明,‘党’总是在国家之前——我们有这个党,它有着无上权威,但总在幕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人们意识到,在中国的成功故事之下存在着诸多紧张和对抗,也提醒人们,中国要转变为议会民主可能会进一步深化这些矛盾。
有许多国家,甚至在形式上拥有着正规民主的国家,其实也有不少是半秘密的小集团在控制着政府。例如在种族隔离下的南非就有秘密兄弟会(Broederbond)。但让中国这种情况独一无二的是,在公共和隐秘领域中,党的双重权力都被制度化了。
不论在党和国家机关以致大公司中,对重要职位的提名皆由中组部这个党的组织来首先提出。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北京,但却找不到电话号码,也没有路牌指示其所在位置。组织的决定一旦落实,便会送到合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大家行礼如仪地通过投票加以确认。相同地,“先党后国”的做法发生在每一层面,包括基本的经济政策,也是先在党内辩论,然后再由政府部门实施。党与国家之间的落差在反腐斗争中更加昭然若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党组织调查案件时无需受到法律的限制:嫌犯可以被绑架,被暴力质询,及被关押长达六个月之久。最后如何被定罪,不仅仅要看犯罪事实,还要看不同的党内派别之间在幕后复杂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如果这样权衡下来认为嫌犯有罪,这才会送交国家法律体系,其实所有的事都已尘埃落定,审讯只是走个形式——只有判决(有时)还有酙酌的余地。
讽刺在于党自身才是所有腐败的根源,因为它复杂的运作都隐藏在公众监督之外。在圈内,党的高层与国家机关以至行业大佬们,都通过某种专属的「红色机器」的电话网络来沟通联系——有这样一个不会公开的电话号码便清楚无比地体现某人的地位。有一位副部长曾告诉马利德,“超过半数从‘红色机器’接到的来自高层官员的要求无外乎是:‘可否为我的儿子、女儿、外甥、侄子、或好朋友等等找一份工作?’”
在八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上,新的中央权力班子名单便会被钦点地产生——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九名成员。整个甄选过程包含着幕后复杂的商议。代表们之前不会得知谁会被任命,却收到正式邀请要从名单中投票选出新班子,新的管理班子也会在一致通过中诞生。作为规则(也不一定是所有时期的规则),党的最高权力核心有三个: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后两个位置远比第一个重要。而人民解放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实体,遵循毛泽东所说的“党指挥枪”。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军队一般被假定为非政治性的、中立地维护宪政秩序;但对中共来说,如此去政治化的军队是可以想见的最大的威胁,因为军队正是国家要受制于党的保证。即使运作得当,这样的结构关系也不得不依赖着武力和协议的脆弱平衡。因为党是在法外行事,因此有一套复杂的不成文的规则来确保人们按照党的决定行动。
党国的概念不能适当处理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复杂性:因为在党与国之间常常存着鸿沟,而党又像是国家的另一重影子。异见人士呼吁与国家有一定距离的新政治,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党就是这距离:党对国家、机制和运作都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仿佛它们无时无刻都需要党来控制和监督。真正的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充分地接受过国家:它接受的是要有代理的必要、免于法律的约朿,以使它有足够权力来指导国家的所作所为。
这个模式肯定会被批评为不民主。在作为民主模式的伦理—政治的取向下,党至少在形式上应当低于国家机制,它才能符合“民主论”。这里其实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在“自由”社会中,统治与被统治是在“去政治化”的经济财产领域及管理权力下运作的。那么中国共产党要与国家机器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没有法律约束下行使其权力不是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可能吗:“非法”活动并不一定是要满足市场的利益,有时候,也是为了满足工人的利益。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到中国的时候,本能地反应是中国应跟随西方银行的危机处理方案,严格削减投放给想要进一步扩张的公司的贷款。但非正式地,也没有法律的合法允许下,中国共产党只简单地要求银行放宽信贷,结果成功地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另一个例子,西方政府投诉说,其绿色能源产业未能在发展绿色科技上与中国竞争,皆因中国公司获得了政府财政上的资助。但这样做究竟有何不妥呢?为何西方不能跟随中国,有样学样呢?
但是中国不是新加坡(在这一方面,新加坡也没有做到):中国不是一个确保社会和谐,将资本主义纳入控制之下的威权政体。每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及少数民族制造的动乱最终要靠警察和军队的镇压才能扑灭。难怪官方的宣传一直都在高唱“和谐社会”的论调:这种反复强调只是个反面证明。我们应该谨记斯大林式诠释的基本原理:鉴于官方媒体不会公开报道问题,所以最有效地感受问题的方式就是看国营媒体在反复强调什么:越是高歌“和谐”,现实中就有越多的混乱和对抗。中国已经在失控的边缘。危机一触即发。
译注1:原文是Big Other,经达人指点,是一个有哲学含义的专用词,应翻为“大他者”,查询了一下这个词的含义,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单词/文字都认识,但是合并起来的解释还是不理解。恕译者才疏学浅,如想追根究底,请自行查阅书籍或相关资料。
译注2:Founding Crime也被译为“建国之罪”,这里意译为“原罪”,虽有附会基督教之嫌,但我仍然认为是最贴切的译法。
译注3:此处应指在1989年未经合法程序即被清洗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译注4:这里的翻译是参照过去齐泽克对《国王的新衣》故事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释而作的,他指出国王的新衣重点不在国王没有穿衣,而是所有人都知道国王没有穿(新)衣下仍然伪装他有穿衣来办,他们已毫不介意国王没有穿衣。
译注5:这里的natioanal assembly应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作者简介: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被部分评论家认为是“真正的左派”。
说明:本文继续开放校对,如有错误,欢迎留言或来信指出。
点击这里订阅及墙内看译者;
看不到相关阅读?点击这里一键翻墙
相关阅读
- 安装适合你的浏览器的红杏插件一键翻墙
- 翻墙看《译者》https://yyii.org
-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订阅《译者》;
-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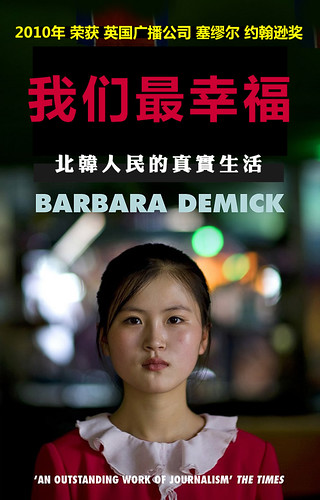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