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Qaddafi's Legacy
作者:JASON PACK
发表:2011年10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原文配图:军事政变刚成功后的年轻的卡扎菲。】
穆阿穆尔・卡扎菲死了。一群曾被他嘲笑为"鼠辈"的革命者把他像老鼠一样从下水道里拖了出来。
就这样,利比亚人终于翻过了自1969年9月1日开始的历史篇章。当时,强人卡扎菲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取得了权力,宣告成立一个致力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和(阿拉伯)统一的"的纳赛尔主义共和国。
最终,尽管卡扎菲进行了洋洋自得的意识形态革命,并宣称,他是代表热爱他的人民进行统治,但是因为国家核心的安全职位被分配给了他的儿子们和信得过的效忠者,他的政权已经成为了旧式的家族独裁政权。现在他死了,利比亚人民获得了一把双刃剑:一次从头开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机会。
跟旧体系的残余势力仍紧握权力的突尼斯和埃及不同,之前的利比亚政权的权力基础已经被完全毁坏。很多过渡政府的高官曾占据着卡扎菲统治下的部长职位是事实,但是不要被这个现象给蒙骗了。8个月的冲突已经彻底地摧毁了他们曾服务过的旧的社会力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不是利比亚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转型。尽管今日利比亚的源头是一场标准的军事政变,但是实际上在1969年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革命"代表的是一种突尼斯脱离法国的独立,和纳赛尔在1952年的埃及政变都没有经历过的社会动荡。再追根溯源的话,跟任何其它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的经历相比,利比亚在意大利移民殖民主义下的经历所具有的侵害性和破坏性都要远大于前者。甚至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移民殖民主义与利比亚的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后者利用法西斯政策更成功地将既有的公民社会连根拔起,利比亚四分五裂、互相敌对。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利比亚根本不存在正常运转的全国性的官僚机构和民间机构。突尼斯人和埃及人有他们自己的军队、工会、和强烈的超越了本地身份的国家身份认同感。在利比亚,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全国性机构和真正的国家理念建构――利比亚人首先觉得自己是的黎波里人、米苏塔拉人、班加西人、或者津坦人。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利比亚人都急切地盼望国家统一――人们对前卡扎菲时期的Senussi旗帜的热爱(甚至在旗帜的发源地,东利比亚的昔兰尼卡省之外也是这样)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除了利比亚政权的一些部族要塞,比如巴尼・瓦利德和苏尔特,利比亚的革命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全国范围的底层运动。
今天,当你走过的黎波里街道的时候,这种混杂的遗产表现得十分明显。来自米苏塔拉、津坦和贾杜等地的民兵――都有各自的指挥体系――在街上维持秩序。尽管每个民兵组织都正式地向国家过渡委员会(NTC)表示过自己的忠诚,但是这些战士首先是对他们当地的组织和领导效忠。这些组织和领导都是在过去6个月里自发地出现的,并建立了让人惊讶的凝聚力和情感纽带。全国过渡委员会宣称自己支持组建以邻里为基础的民兵组织,因为这些可信的当地的和部族的网络不会被卡扎菲支持者渗透。实际上,利比亚的革命是一系列的地方起义――而全国过渡委员会则宣称自己已经把它们缝合在了一起。
让我们衷心希望新的利比亚政府已经学会了缝缝补补,因为接下来的任务――建国――也许会比推翻世界上最有适应能力的独裁者还要困难。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当地神话来讲述它们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班加西人吹嘘自己是如何第一个抛掉了卡扎菲的枷锁。米苏塔拉人则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经受了更大的艰难困苦,以更强大的军事凝聚力浴血战斗――而现在,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打倒了卡扎菲。来自纳福沙山区的柏柏尔人抱怨他们的种族身份如何受到了卡扎菲的压制,以及来自这些崎岖山区的勇士的精神是叛军取胜多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个组织都在忙着编造他们如何一直抵抗卡扎菲的神话。在盖尔杨,一份单版的《新闻》日报复印件连载了一个可疑的故事。故事说的是这个处在战略要点的城镇,是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全面反卡扎菲街头抗议的起源地。在班加西,当地居民都在引述一个更为真实的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有不少居民(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帮助下)发动了针对政权的小范围游击战。在的黎波里,新的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把自己同刺杀已故上校的圣战努力联系在一起。
对卡扎菲以及他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厌恶,把所有这些迥然不同的各地族群联合在一起。在利比亚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卡扎菲的头像,但是大部分的利比亚人跟那些可以把他们的抱怨转达给卡扎菲家族的人相差好几个等级。在当前的本地的权力安排中,情况则正好相反。比如在米苏塔拉的生意人群体中,普通居民现在跟当地政治和民兵组织的首领只相差一个等级。在柏柏尔山区里的部落成员也是如此。他们对当地的领导者感到亲近和信任,这些领导者都是从传统的多样的部落和新近自发产生的革命中诞生的。
这个情况似乎意味着,利比亚人将开始一个新的关于政府管理的大胆试验――而他们的突尼斯和埃及兄弟不大会接受这样的实验。在卡扎菲的统治下,中央控制着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今天的利比亚革命者想拥有本地的可靠的权力和机构,通过法治管理,但不是以西方的那种方式。而且,他们很多人都希望重新振兴传统的血缘关系和本地网络,以此创造一个可以联系利比亚人以及联系利比亚人和国家的社会网。
2011年的利比亚革命中的一大讽刺是,这些利用传统的团结纽带、自发形成的地方委员会是卡扎菲曾在自己的《绿宝书》中宣讲过,却从未实践过的东西。"到处都有委员会"的卡扎菲语录至今仍然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告示板上看到。但是,这位兄弟领袖绝没有想到,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到来,并不是因为他的虚伪规劝,而是对这些虚伪规劝坚决反对的结果。时间将证明利比亚人是否能保住这个成果。
相关阅读:
《外交学者》中国的独裁者情结
就这样,利比亚人终于翻过了自1969年9月1日开始的历史篇章。当时,强人卡扎菲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取得了权力,宣告成立一个致力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和(阿拉伯)统一的"的纳赛尔主义共和国。
最终,尽管卡扎菲进行了洋洋自得的意识形态革命,并宣称,他是代表热爱他的人民进行统治,但是因为国家核心的安全职位被分配给了他的儿子们和信得过的效忠者,他的政权已经成为了旧式的家族独裁政权。现在他死了,利比亚人民获得了一把双刃剑:一次从头开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机会。
跟旧体系的残余势力仍紧握权力的突尼斯和埃及不同,之前的利比亚政权的权力基础已经被完全毁坏。很多过渡政府的高官曾占据着卡扎菲统治下的部长职位是事实,但是不要被这个现象给蒙骗了。8个月的冲突已经彻底地摧毁了他们曾服务过的旧的社会力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不是利比亚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转型。尽管今日利比亚的源头是一场标准的军事政变,但是实际上在1969年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革命"代表的是一种突尼斯脱离法国的独立,和纳赛尔在1952年的埃及政变都没有经历过的社会动荡。再追根溯源的话,跟任何其它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的经历相比,利比亚在意大利移民殖民主义下的经历所具有的侵害性和破坏性都要远大于前者。甚至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移民殖民主义与利比亚的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后者利用法西斯政策更成功地将既有的公民社会连根拔起,利比亚四分五裂、互相敌对。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利比亚根本不存在正常运转的全国性的官僚机构和民间机构。突尼斯人和埃及人有他们自己的军队、工会、和强烈的超越了本地身份的国家身份认同感。在利比亚,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全国性机构和真正的国家理念建构――利比亚人首先觉得自己是的黎波里人、米苏塔拉人、班加西人、或者津坦人。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利比亚人都急切地盼望国家统一――人们对前卡扎菲时期的Senussi旗帜的热爱(甚至在旗帜的发源地,东利比亚的昔兰尼卡省之外也是这样)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除了利比亚政权的一些部族要塞,比如巴尼・瓦利德和苏尔特,利比亚的革命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全国范围的底层运动。
今天,当你走过的黎波里街道的时候,这种混杂的遗产表现得十分明显。来自米苏塔拉、津坦和贾杜等地的民兵――都有各自的指挥体系――在街上维持秩序。尽管每个民兵组织都正式地向国家过渡委员会(NTC)表示过自己的忠诚,但是这些战士首先是对他们当地的组织和领导效忠。这些组织和领导都是在过去6个月里自发地出现的,并建立了让人惊讶的凝聚力和情感纽带。全国过渡委员会宣称自己支持组建以邻里为基础的民兵组织,因为这些可信的当地的和部族的网络不会被卡扎菲支持者渗透。实际上,利比亚的革命是一系列的地方起义――而全国过渡委员会则宣称自己已经把它们缝合在了一起。
让我们衷心希望新的利比亚政府已经学会了缝缝补补,因为接下来的任务――建国――也许会比推翻世界上最有适应能力的独裁者还要困难。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当地神话来讲述它们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班加西人吹嘘自己是如何第一个抛掉了卡扎菲的枷锁。米苏塔拉人则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经受了更大的艰难困苦,以更强大的军事凝聚力浴血战斗――而现在,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打倒了卡扎菲。来自纳福沙山区的柏柏尔人抱怨他们的种族身份如何受到了卡扎菲的压制,以及来自这些崎岖山区的勇士的精神是叛军取胜多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个组织都在忙着编造他们如何一直抵抗卡扎菲的神话。在盖尔杨,一份单版的《新闻》日报复印件连载了一个可疑的故事。故事说的是这个处在战略要点的城镇,是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全面反卡扎菲街头抗议的起源地。在班加西,当地居民都在引述一个更为真实的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有不少居民(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帮助下)发动了针对政权的小范围游击战。在的黎波里,新的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把自己同刺杀已故上校的圣战努力联系在一起。
对卡扎菲以及他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厌恶,把所有这些迥然不同的各地族群联合在一起。在利比亚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卡扎菲的头像,但是大部分的利比亚人跟那些可以把他们的抱怨转达给卡扎菲家族的人相差好几个等级。在当前的本地的权力安排中,情况则正好相反。比如在米苏塔拉的生意人群体中,普通居民现在跟当地政治和民兵组织的首领只相差一个等级。在柏柏尔山区里的部落成员也是如此。他们对当地的领导者感到亲近和信任,这些领导者都是从传统的多样的部落和新近自发产生的革命中诞生的。
这个情况似乎意味着,利比亚人将开始一个新的关于政府管理的大胆试验――而他们的突尼斯和埃及兄弟不大会接受这样的实验。在卡扎菲的统治下,中央控制着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今天的利比亚革命者想拥有本地的可靠的权力和机构,通过法治管理,但不是以西方的那种方式。而且,他们很多人都希望重新振兴传统的血缘关系和本地网络,以此创造一个可以联系利比亚人以及联系利比亚人和国家的社会网。
2011年的利比亚革命中的一大讽刺是,这些利用传统的团结纽带、自发形成的地方委员会是卡扎菲曾在自己的《绿宝书》中宣讲过,却从未实践过的东西。"到处都有委员会"的卡扎菲语录至今仍然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告示板上看到。但是,这位兄弟领袖绝没有想到,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到来,并不是因为他的虚伪规劝,而是对这些虚伪规劝坚决反对的结果。时间将证明利比亚人是否能保住这个成果。
相关阅读:
《外交学者》中国的独裁者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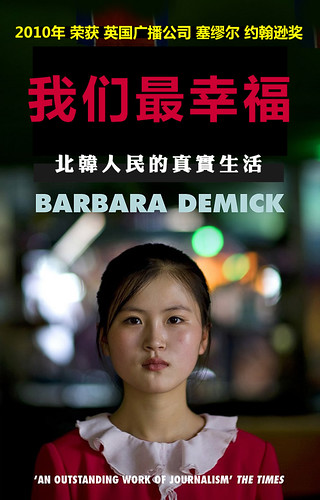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