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Arab Spring is 2011, not 1989
作者: Jean-Marie Guéhenno
时间:2011.4.26 星期二
译者:阿拉伯的劳伦斯
阿拉伯世界没有民主转型能力的陈腔滥调已经被阿拉伯革命的现实所打破。但是另一种滑稽的说法却正在取代它:根据这种新的说法,那些通过脸书或者推特动员起来的,聚集在开罗、班加西或者大马士革的人群,是西方民主理想传播的最新实例;当“其他的崛起”挑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的时候,西方仍将继续决定世界的政治事务。
在这个乐观的说法里,1989年和2011年只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章节。它用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把对民主的政治需求同企业家和新技术的变革力量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震撼了阿拉伯世界的运动同结束苏联帝国的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阿拉伯之春与民主有关,但是同时也与正义和公平有关。因为在这些社会里,有着数百万没有工作的青年男女——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低于每天两美元——他们渴求正义跟渴求民主的愿望一样强烈。
正如我听到一位资深阿拉伯外交家说的,今天的革命反对的既是独裁者,也是“既得利益者(profiteers)”。这些运动对外国干涉有着深深的怀疑,而许多年来一直和独裁者和既得利益者保持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会被这些运动利用,但是不会被信任,或将它们当做1989年时曾被景仰的模版。
我们的中东政策的影响非常广泛。好消息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正义、发展和再分配等实际问题上,有助于让公共讨论远离那些由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所宣传的,回到过去神话中的伊斯兰王国的梦想。
用法国学者奥利维尔 罗伊(Olivier Roy)的话说,阿拉伯的革命也许会成为第一次“后伊斯兰主义”革命。但是,只有当我们西方世界的人去接受伊斯兰的价值观——就像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的价值观一样,对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作为政治辩论的一部分(而不是辩论的中心)的时候,这才可以成为现实。
我们越是将对抗伊斯兰运动的世俗力量极端化,世俗力量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小。必须摒弃把阿拉伯世界的事务定义为一场温和派和强硬派的战斗的幻觉。欧洲和美国如果结束他们“点单式民主”的政策,并开始与哈马斯或真主党这样的运动展开对话,就能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方面都赞同他们的观点。
优先考虑把穆斯林兄弟会和相关的组织引入主流政治圈来,而不是试图孤立它们。这个考虑十分必要。因为对正义的追求将会带来这样的要求:目前的精英——尤其是安全部门——不仅要交出他们对权力的控制,还要交出对经济的掌控。而这个要求最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动荡。
从2000年以来,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和以色列-阿拉伯之间的冲突通常采取善意忽视的态度,一个更加民主的阿拉伯世界将会更难以容忍这种态度。对那些支持依照与国际法和“两个国家”解决方案获得冲突决议的国家来说,这不应当被看作一种威胁。但是它将会要求对过去十年的政策进行“复位”。
最后,正如我们发现的,2011年的情况跟1989年不同。我们不再是值得信任的参照,我们将要在一片未知的水域里航行:我们在利比亚的行动的道德感在终结的时候也许会比开始的时候要少一些。政治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而我们也会受到去挑选胜利者,操纵最后的结果的诱惑(尤其是在石油丰富的国家)。
但是,对我们的长期的立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自从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的前途不断地被外国人决定。外界强国需要证明,他们这次是真的愿意支持本土成长起来的的政治进程。
西方要能接受它再也不是主要的参与者的局面。但是它也不必成为一个消极的、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在参与和克制中寻求平衡将成为这一新阶段的政策挑战。
在利比亚,也许还在其它国家,联合国为寻找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而积极进行参与,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提供正义和与大国政治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大国政治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它们,没有任何政治进程会有一个可持续的结果。
Jean-Marie Guehnno是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人权对话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的董事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索尔兹曼研究所(Saltzman Institute)专业实践的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1年4月21日的《纽约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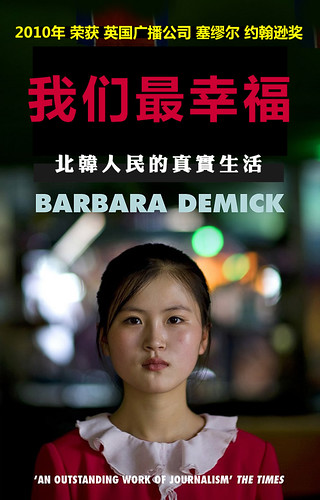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