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中国的医疗私有化让看病人排长队,并感觉受挫
作者:David Pierson
发表时间:2010/02/11
译者:@mhisun
校对:@xiaomi2020 @Wayne
原文链接: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la-fi-china-hospital11-2010feb11,0,6851562,print.story
对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女子和她生病的父亲来说,在北京最知名的医院仅仅预约就是长达一星期的昼夜折磨。
最好的医生的预约号通常在日出前就被一抢而空。在医院六个挂号窗口前队伍至少前一天就排开了。Nie父亲的病需要看几个专科专家,他由于太虚弱而无法自己排队。Nie 毫无选择只能每夜去占位置挂号,这样早上她才能挂到一个号。
她周围有几百个病人和家属挤满了灯光昏暗网球场大小的挂号大厅,而每晚这里变为供人睡觉的营地。一位来自产煤乡镇的女子在一堆夹克上打起盹来,她准备预约肝病专科医生。一个门卫坐在一叠新京报上,为他患有肾病的表亲占位排队。很多排队的人靠打牌,织毛衣或者打盹来打发时间。当有人要去洗手间或是过街买食物时,队伍里邻座的人会帮他们看好位置。
Nie坐火车从250英里外的内蒙古远道而来,她很幸运排在队伍的前头,很有机会能预约到一位梦寐以求的医疗专家,即时就这样也不能打包票。那些有门道有钱的病人不会为排队而费心。黄牛冒充病人排队或者和黑心的挂号工作人员串通抢光队伍空位并卖给出最高价的购买者。
“整一个星期我们都在排队,”20岁的Nie说。“我们还能怎么办?”
正当美国着手进行医改以给更多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时,中国却因为抛弃医疗系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西方式的私有化所而痛苦挣扎。政府致力于医疗体系现代化并淡化北京的角色,这导致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大幅减少,农村医疗系统尤其受到影响。
其结果是很多美国人所熟悉的:有良好医疗保险或是充裕存款的病人在最好的医疗设施得到一流的服务,而数百万的无医保的和贫穷的患者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的疾病足以使他们破产。医院也为自保而变得冷酷无情。医疗成本在飙升,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医院鼓励医生给病人开出昂贵处方药物和要求病人进行不必要检查的行为。
考虑到摇摇欲坠的医疗体系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央政府拨出了1240亿的资金进行医改,主要旨在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无法解决国家医疗问题,不仅对国内人口占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而且对世界也是灾难性的,因为传染性疾病例如H1N1流感,渐渐威胁到全世界。
“中国医疗系统的目标是应该是医疗服务的普及化”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Jonathan Samet说,“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考虑如何服务其公民。”
Nie和她的家人生活在省会城市呼和浩特的农村边远地区,呼和浩特是中国中北地区的两片山脉间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直到去年春天,他们的生活还是平平常常。她的父亲是位卡车司机,母亲是附近餐馆里的厨师。家里依靠每个月350美元的收入,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
而四月份Nie的父亲突然背部疼痛,无法开车。他开始感觉昏睡无力,体重骤减。Nie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帮助家里维持生计。
六个月后,村里诊所和县里医院的医生仍然无法确诊。家里决定,唯一希望是去北京找专家医治。Nie的父亲知道北京协和医院并相信那能治好病。
“那是最好的,工薪阶层都能看病,”Nie的44岁父亲Nie Gencheng说。
家里凑了全部积蓄--几千美元--就这样,父亲和女儿踏上了去北京的路。而他们当地的医保在北京不能用,需要自行付钱请专家看病。
几十年来,地处首都中心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医疗质量历来被认为是国内一流的。这家著名医院成立于192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并依附于一所知名的医科大学,它五彩的瓦片屋顶见证了中国光辉的过去。
但随着农村医疗体系的解体,农民蜂拥至城市,挤满了像协和医院这样的医疗中心,这儿每天有来自全国各省的大约4000名患者。
“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Zhou Shengli说,该医院也是一家国内顶尖医院,每天那也有长长的队伍和大量黄牛。“北京这么点医院不可能治疗13亿的患者。”
医疗需求的激增助长了黑市的成长。成堆的黄牛游荡在中国的主要医院,以几百美元的高价兜售高价预约门诊号--其价格相当于普通农民几个月的收入。尽管政府定期整顿,这些骗子仍就在北京协和医院挂号大厅(一幢低矮的一层医院主楼附楼)外自由地买卖门诊号。
“唐医生,唐医生,谁要唐医生的门诊号?风湿免疫科,”一男子,近日某晚当着门卫的面向过路者叫卖。其他黄牛则拿出手写的名片,担保能挂到任何医生的号。
Nie辞掉了餐馆的工作陪父亲来看病。这是她第一次到首都。她和父亲在旅馆租了两张床,每晚10美元,盘算着如何挂号。
电话挂号根本没用;医院每天只有200个电话预约名额。几年前曾经实行过在线挂号,结果几小时内病人就订完了半年的门诊号。
先来先治病,Nie也不得不排起队了。她父亲每天穿着同一条破烂的细条纹裤子和运动上衣,只能卯足力气和她呆一下午。Nie则晚上独自一人排队,买了泡沫塑料垫着睡觉。
头一天,她在旅馆呆到下午,然后到挂号大厅准备在那过夜。她在父亲准备看病的那科室前和门卫签了到,到最短的队伍中找个了地。早上醒来,轮到她到挂号窗口前,电脑打印出一张那天骨科预约的白色门诊号子。第二天,她挂了疼痛专科,下一天早晨是心脏科。结果没一个医生知道他父亲得了什么病。
“每次都是一样的答复,”Nie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小心照顾你爸。”
Nie和她父亲变得沮丧起来。他们确信应该去看神经科主治医师--最难挂号的专家门诊。他们唯一的希望是Nie要排到队伍前头。
在挂号大厅里过了三个晚上,Nie决定白天也在外面打地铺不回旅馆了。她在神经科那留了名,带着自己的物品坐在其中一个挂号窗口前。
但第二天早上,挂号的工作人员告诉她神经科主治医师那天不上班。她不得不等到第二天给父亲挂号。Nie不想挂其他医生的,于是又一次和门卫签了到,在一排队伍前头找了地过夜排队。
夜晚,时间安静地过去,偶尔被一两下鼾声打断。早上六点,人群被警卫惊醒,要求他们队伍排直并归还租用的折叠椅。刺耳的广播划破了安静的空气,电子屏幕在眼前闪烁着,显示着当日的医师科室安排。
随着外面更多人聚集起来,气氛越发紧张。一警卫冲着一女子大喊,怀疑她是个黄牛,一把抓过她的身份证丢在了地上。
“你这个农民!”这女人骂回去,目的是羞辱警卫的社会地位。
早上六点半,挂号大厅的工作人员撤掉了“没有服务”的牌子,要队伍往前走。
Nie的眼睛由于熬夜肿胀起来,她收拾了下东西,移向窗口。她说要挂神经科,工作人员给了张白色的号子。看着号子上的医生名字,她垂下了肩叹了口气。
“这个人只是我们的第三选择。”她说,由于精疲力尽而无法拒绝这个门诊的预约。
她本以为排在队伍前面就终于能能让这套系统为我所用。但黄牛也许早就买完了她和她父亲想要的那些个号子;又或者是其他队伍前面那几个比我快。总之,她只能怪自己了。
“也许我还不够快吧,”Nie说道。
david.pierson@latimes.com
时报北京记者站 Nicole Liu 报道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最新消息”、“译者@mhisun的个人专辑”、“译者频道—看中国”、“LA时报”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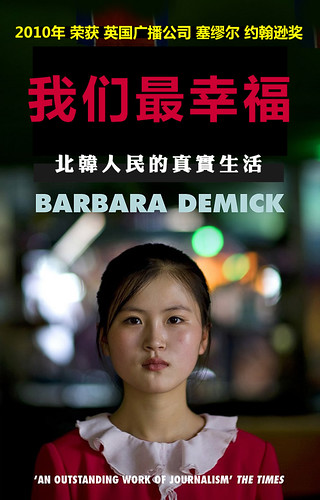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