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邮件到xiaomi2020@gmail.com为 你的朋友订阅墙外博客:《译者》。 We Are Together.
使用GREADER在墙内订阅 《译者》:http://feeds.feedburner.com/yizhe (用https打开)
译者文库总索引:http://zxc9.com/2z0001《参 与译者的多种方式》:http://zxc9.com/Uo0001
原文:民主杂志:一种新的权利意识?
译文:Journal of Democracy :A New Rights Consciousness?
原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09年7月(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专刊)
作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译者:推特ID:hsinwang1982
校对:推特ID:Freeman7777
作者简介: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哈佛大学政治学系Henry Rosovsky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她是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2007)一书的合编者,并著有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2006)。
尽管天安门的反抗活动遭到了残忍的镇压,但由于种种原因,接下来的20年中,中国大众抗议活动发生的频率仍然稳步上升。这些被越来越多地贴上“合法权利”标签的抗议活动几乎遍及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很多观察家据此声称,“处于上升态势的权利意识”的出现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威以及政权持久性形成了一种萌芽状态民主的挑战(protodemocratic challenge)。
本文之后四篇文章的作者对受到侵害的工人和农民、互联网活动人士以及新“中产阶级”等来自中国不同部门的抗议者是否实际上已对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进行了评估。天安门反抗活动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许多学者将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的希望寄托在工人与学生的结盟身上。在中国,如同波兰那样,与知识界异议人士并肩作战的工人行动看上去能够削弱共产主义体制。然而20年过去后,出现团结工会般剧情——由工人领导的推翻失去民心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多阶级联盟(multiclass coalition)——的前景仍然渺茫。李静君(Ching Kwan Lee)和伊莱·弗里德曼(Eli Firedman)在其文章中指出,纵观困扰当代中国的汹涌劳工抗议活动,“没有任何动员的迹象表明劳工行动会跨越阶层和地区”。纵使在工人中出现了所谓的“权利意识的增长”,但两位作者还是认为“曾经使工人能够参与学生群体一起进行反抗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已不复存在”。同样,在农村,欧博文(Kevin O’Brien)发现“跨越阶级界限的合作”仍旧“缺乏”。农村抗议有助于抑制基层干部的暴政行为,但这无法预示政权转型即将启动。相反,欧博文将中国当局乐于容忍范围如此之大的农村抗议视为共产党政权自信和具有韧性的象征。
如果北京当局已设法驯服了1989年在中东欧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旧的”社会阶级,在面对20年前的中国完全不存在的网络行动者和新中产阶级等社会力量所发起的侵蚀式挑战时,当局还会同样擅长处理吗?在杨国斌看来,网络抗争能够提高公民的勇气和辨别力,他认为这种转变是任何民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杨国斌用来证明网络行动政治影响力不断增长的证据(包括政府取消一项过时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表明,通过同情而理智地回应网络聊天室发出的抱怨,威权国家也许已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条颇有效的长生之道。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电子通讯为公民的行为和态度提供了关键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不仅能用来预测和清除潜在的挑战,也可以通过制定直接针对公众痛苦的政策来提高治理绩效。Jeffery Wasserstrom的文章也强调了现今的通讯技术(尤其是短信)对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发起的避邻运动(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的重要性。同时,Wasserstrom也警告了以下荒谬的假设:这些对抗预示着中国的民主化即将启动。相反,他指出,这些行为正朝一个更平庸的方向发展:一个不断成长的维护和提升社区生活质量的中产阶级。
本期刊物中的讨论表明,“常态政治”(politics as usual)这一表达方式而非由一个新生的公民社会主张免于国家侵入的自主性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民主要求更有利于解释当代中国抗议者的权利话语。今天的抗议者所运用的权利修辞延续了中国抗议者偏好使用官方话语来表达自己痛苦的传统。准确地说,这是为了强调其抗议行为无意挑战国家的合法性。即使充满了讽刺性的用以反映国家政策初衷和政治执行情况落差的抗议修辞(例如,杨国斌在文章中提到的网络活动人士),这种能够未使用官方认可的话语修辞的情况恰好说明了抗议者游走在国家规定的合法话语界限的边缘,而没有选择有政治权威性的其他话语。与此相似,抗议磁悬浮高速铁路扩建的上海抗议者将自己的徒步抗议称为“和谐散步”。在嘲讽政府“和谐社会”这一口号的同时,他们也表明了对国家所提倡的话语的依附。
我倾向于用“规则意识”(rules consciousness)这一旧瓶装新酒的概念来描述这些抗议,而非反映了一种新被发现的“权利意识”。这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常规大众抗议的根基。如同帝制时代的抗议提及“天命”(Mandate of Heaven)、中华民国时代的抗议提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毛泽东时代的抗议提及群众路线(mass line)和“造反有理”(right to rebel),今天的抗议者将需求置于已为当今中国国家承认并加以推广的“合法权利”(legal rights)下。
不论这些抗议有多么声势浩大(某些抗议还出现了暴力),参与其中的人通常不遗余力地表达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尽管“公民”发出“权利”要求的话语取代了毛泽东时代“同志”表达“革命”语言,抗议者的心态以及抗议者同威权国家的关系都说明今天的抗议与过去的抗议并无本质区别。
抗议的遗产
中国号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抗议事件的国家之一,也是抗议传统最为悠久的国家。经过民间故事、传说、地方戏曲的传播,几个世纪以来为大众熟悉的抗争题材的剧目一直是告诫专制政治体制善待百姓的主要工具。在某些非常规状态下,地方抗议活动可能升级为大规模的起义,这种类型的中国历史都是非常著名的。但它对异端意识形态、超凡魅力型起义领袖、蔓延的经济危机、外国威胁、反应迟钝且不称职的中央政府进行的催化剂式的结合对王朝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威胁。而这样的结合并不多见。
尽管对共产主义中国的体制进行任何与帝制中国的体制有关的预测都带有明显的鲁莽性,但考察某些历史相似性是很有价值的。随着早先不为人知的“权利意识”的出现,当今的学者习惯称道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但根据诉讼档案的记载,帝国和民国时期就有众多的集体行动的例子。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地方志(Local gazetteers)确认了,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乡村社会的各部门通常都会诉诸法庭。法律途径是农民认可的促进集体利益实现的手段。一旦这样的努力未能产生预期效果,抗议活动通常会继续进行。与近期欧博文观察的很多农村抗议相似,为了谴责地方官员的非法和贪腐行为,帝制时代的抗议往往以呈送主要用样板用语写成的、渴求中央政府权威与慈爱的请愿书开始(引用帝国法令和大清例律【the Qing legal code】)。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帝制时代以来的中国未发生改变。过去20年,中国的确经历了让人震惊且难以想象的转变,过去200年的变化就更不要说了。我的观点只是认为,针对较低层级政府且限定在中央政府语言框架里的(尽管语言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以反映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的重要差别)遍布广泛的大众抗议更像是常规政治的象征,它并没预示国家—社会关系会出现某种结构性转变。在像中国这样的选举从未将民意转达给政治领导层的威权体制下,反而是抗议活动通常实现了这一目的。只要中央政府同情且机智地回应大众抗议中表达的痛苦,例如像2006年历史性地废除农业税那样,它会出现增强而不是衰落的势头。
当然,测量生活在表达反抗有着巨大风险的威权体制下的公众他们真正的感性意义上的政治看法即使可行,也是非常困难的。不管内心是否认可共产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中国的抗议者通常在行动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认可那种合法性的。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长期强调“正当”(orthopraxy)(合适的行动)胜过“正统”(orthodoxy)(合适的观念)的国家,对政治权威的公开顺从似乎对维护体制尤其有重要作用。
延伸阅读
相关阅读:
译者的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2000-2009专题(加超链)
译者@hsinwang1982的个人专辑(加超链)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 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XX”、“YY”、“ZZ”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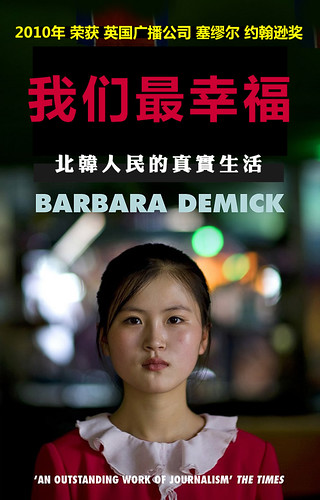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