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By David Welker
作者戴维•威尔克,国际卡车司机协会,高级项目协调人
本文是David Welker在2006年2月2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所举办的Hearing on Major Intern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听证会)Panel 3: China's Internal Unrest: Worker Demonstrations, Civil Disobedience, Riots and Other Disorder, and the Prognosis for the Future上所作的证词
原文下载,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6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6_02_02wrts/06_02_02_welker_david.pdf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首先我必须对所有委员邀请我来参加这场听证会表示感谢。谢谢听证会共同主席, Wortzel 委员和Reinsch委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的良好工作持续在美—中关系的艰难问题上通报辩论并且教导国会以及美国公众。
我感谢委员会给我这样的机会,能来这里讲一下中国所发生的工人动乱以及该国在共产党统治下长期稳定的前景这些议题。
当观察中国当前体制时,人们不得不怀疑经济学家的语言在此处是否能派得上用场。这个国家是由一个自谓为“共产主义的”一党制的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a one-party authoritarian dictatorship that calls itself “communis”)所运行的,但却容忍了一个杂种般的市场经济,其中混合了某些最为重商主义的政策(mercantilist policies),某些最为无情的自由放任的措施(laissez-faire practices)以及某些以“改革”为幌子的厚颜无耻的国家计划的做法。并且到目前为止这个体制已经违背了(外界对其的)绝大多数期盼——可能还违背了经济引力(economic gravity)的重要意义超过25年的时间了。党已经放弃了以革命热忱作为其指导力量而钟意于增长以及不平等作为其主要原则。
然而,过去的表现不是未来结果的征兆。
事实上,对于中国近期的表现我们也一样知道的不是很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修改显示了即便是宏观经济的图象也是相当模糊的。就像纽约Roubini环球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塞特塞尔(Brad Setser)在其私人网志所做的一个评论那样:分母的变动意味着每个“由GDP构成的”数字都需要被修正——然而它却并没有提高任何分子的数值。一份出自官方的国家发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的研究报告预测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在8.5%到9%之间,但是也警告通胀会在今年回归。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指出“一些经济学家说这家官方智囊组织正在释放出令人困惑的信号来,这反映出官方对于如何使经济增长走上轨道的不确定性。”难怪许多观察家都被此情形给搞糊涂了。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其2003的专著《中国经济地带的断层》(《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中文版把书名翻译为《裂缝:中国经济面临的八大敌人》)中,兰德公司宣布要采取一种“反流行的视角(countervailing perspective)来看待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流行共识性的看法”,这种共识性的看法就是“中国的经济在不确定的未来可能会维持高比例的增长。”我认为他们挑选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断层”的研究领域,这些潜伏在表面之下的“断层”对于中国经济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该报告对于中国设想的增长路径的潜在风险确认了八项具体议题:失业和农村贫困;腐败及其效应;传染性疾病;环境退化;能源价格震荡;国家金融体制以及国有企业的失败;外国投资的缩水;以及“台湾问题和其他可能发生的冲突。”这看起来是份合理的“清单”。
其他的(造成潜在风险的)系列要素由韩东方牵头、提倡劳工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编撰进了一份发表于2005年、题为《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00—2004)》(《The Workers Movement in China 2000-2004》)并且至今仍未翻译成英文,因此没有在西方观察家中广泛流传的报告中。作者们在该报告中确认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受到在“改革”旗帜下,中共的经济政策影响到的工人团体。值得详细引述的一段内容是:
在该报告所涉及的时期里,参与了工人集体诉求行动的人士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主要由大部分为失业和下岗工人的人士所构成,并且还包括了较少人数的退休以及目前仍在上班的工人。这样的群体通常可以在位于东北、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平原的老工业基地中被找到。他们的职业范围集中于能源、伐木、军工、纺织、钢铁、石头、建筑、制糖以及其他一些工业部门。这些工业就是国有部门改革以及重建的主要目标。
还有一种类型的工人是由那些在各种类型的企业工作、却迄今仍未拥有城市居民户口的人士所构成;这个工人群体被称为“农民工”(“peasant laborers”)。这些工人大部分可以在位于东南沿海地带的经济已开发地区的地方投资或外国投资的私人企业中被找到。
在失业以及下岗工人所采取的集体性行动中,主要的集体性不满有:要求满足他们积极就业的权利;要求得到承诺支付的工资,社会保险缴纳金,集体性报酬;要求提高基本生活保障;要求释放遭到囚禁的工人代表。
中国劳工通讯的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必须首先指出的是,中国工人所面对的窘况,不是什么‘缺乏权利’(‘lack of rights’)的问题而是‘权利被不当取走’(‘expropriation of rights’)的问题 。基于此种现状,在过去一些年里,发生于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已经随着工人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的升高而增加了,并且成为了主要的社会冲突。
许多外国观察家所理解的造成动乱的经济因素与中国劳工通讯或其他的中国公民权利活动者所归纳出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差别可以回溯至他们对于“改革”的基本看法相左上。我认为那种分歧当中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阵营:
一个阵营感觉中国的改革一直在沿着一条崎岖不平但却方向正确的道路行进,而另一阵营则感到“改革开放“自身——党所采取的方法、决定、政策是错误的,并且党所领导的糟糕的执行仅仅只是新添进的一些问题而已。
但是双方阵营的人士当然都会同意当前CCP领导层所采取的改革路径——一种经济上的重建措施,而只对社会保障网提供了很少的支持,且没有伴随使得当局会具有问责性的政治上的重建。因为当前的改革路径加剧了人民以及政府之间的矛盾,那么回答中国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发展壮大、还是进行协商或是继续保持不间断发生的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朗了:当“改革“加速时抗议活动就会增加。
围绕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整个范围的经济变动的疑问在很久以前就在中共内部被解决掉了。现在的问题是会进行何种形式的这类变动以及他们会在什么体制之下得到贯彻既是中国的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又是那些“只有更快的走这条道路”改革的人士与那些支持“不是这种路径”改革的人士所爆发冲突中最为棘手的部分。在中国进入WTO的问题上进行更多讨价还价的时候,党在内部是有讨论的并且哪怕只是党与有公民—思维的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在WTO之下究竟会出现什么“改革”以及那样的改革会带来什么影响的有局限的辩论。江派所进行的内部辩论是让人窒息的并且党的领导集体决定去以猛拉经济作替代发展模式而费力前进,在一党制的行政以及司法架构中没有真正能倾听因所选择的经济发展路径而产生出的难民们的日益升高的声音。党的领导层出现潜在的分裂,其中一派提倡“更少的改革”而更多集中于支持难民们在我看来是相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党出面约束公务员仍然是潜在可能发生的,但是通过腐败富裕起来在保持党的成员忠诚于现有政策上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要素。
我看到中国最大的经济断层出现在一个威权主义政权的橡皮图章式的“立法机关”无法通过一部承认“私有产权”的法律的国家中所谓的“私有化”国家企业的政策断裂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诞生以来,工人们一直被告诉说国家的资产是归集体所有的并且因此个人不仅在他所工作的场所享有一定的资产,国家资产中也有他的一部分。然而在所谓“改革”的名义下,当局现在却说工人对这些资产不拥有所有权,先前党所委派的管理者现在成了国有企业的股东,并且对先前所允诺的工资、福利或退休金或“购买”集体所拥有的设备和资产的开支没有作出赔偿。
在一个无可否认地简单化的对照中,起码在美国当一个像IBM那样的企业单方面变动退休金项目时,工人们进行求助的做法是把公司的这项决议带上法庭以保护他们的权利。在这个IBM的例子中,法院与工人们站在同一边并且公司被迫要支付法院所决定的赔偿。在中国,工人们正在失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遣退金、他们居住的权利,他们在诸如健康保健以及教育上的社会福利,他们的退休金以及集体所有的资产中他们的“股份”。并且没有第三方可以对当权者进行外部的约束。
我感觉对于工人权利“被不当取走”的广泛诉求在短期到中期是一个更大的威胁,相较于对于工人处境处于“被剥削”状态的诉求而言。在“农民工”的例子中,这些外来移民离开了他们位于农村以及农业地区的家庭,想在靠近城市以及沿海一带的制造业区域中求得工资与工作。有着许多因素使他们离开务农生活,譬如:仅能维持生计的租赁土地的生活以及重体力劳动,吸引他们进入工厂的因素有在新的以现金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中有着获得工资的需要。这些农民拥有很强的责任感去把他们的工资送返回家,因此他们可以忍受他们所在工厂的剥削。在国有企业工人的情况中,直到非常近期一直有着一个完整的社会服务网络以及国家所提供的支持。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以及退休人员在他们的处境中以前是相当有保障的,并被党的宣传机关称呼其为中国的“先锋队”(原文是用“elite”,该词翻译成中文时一般对译成“精英”,但考虑到语境,还是使用了“先锋队”这一译名)。这些工人在此时感受到了一种双重失落:首先失去的是他们的工作以及保障,接着失去的是适当的补偿金,使愤怒更是火上浇油并且产生出了一种受欺骗的感觉。农民工在开始时真的是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工资中获得的东西最起码对其是一种临时性的改善。
期盼中国的独立工会在未来会起到的潜在作用就如希望中国出现独立的司法那样来得一样的无望。中华全国总工会(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ACFTU)仅仅是党的控制所有人口的统一战线(United Front)策略的一环而已。工人们知道许多工厂里的工会官员既是党员又是工厂的管理阶层,官方主要是用其来收集劳动力的动向,然后要求其向上汇报。国有企业的工会在工人当中成了一个口头上的笑料。在外国投资的企业里,只有很少的研究表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支工会究竟在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的工会法声称所有外国公司必须允许在他们的工作场所中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支工会。工人日报指出沃尔玛(Wal-mart),以及一大堆其他国际品牌的公司,在遵守工会法方面做得很欠缺。来自中国沃尔玛的发言人刚开始的反应是说该公司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工会并且他们也不想在中国看到有工会成立。这种回答使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以一种高涨的指控说外国公司只会忽视中国的法律。因此党受到了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挑战。碰巧的是,接下来沃尔玛的CEO在北京以公司资金资助了一家大学的某个“研究中心”,他当时也对公司政策作了一番修正:如果工人自己倡议成立工会,公司会答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要求。我把这段话理解成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上层领导人不能授权让沃尔玛的工人们直接地去建立一个分支工会。那暗示说党可以直接或劝阻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某些未具体指明道姓但却有政治上支持的外国企业之内建立工会分支机构。面对党所授权的经营者,党—国当局以及党的工会的勾结、沆瀣一气的现状,工人们对工会是解决他们窘境的部分解决之道不报期待是正当的想法。
大多数工人并不认为集体代表(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在当前的权力架构底下有着任何的权力,因此工会在许多其他国家中带来了处境变化的影响,像在20世纪初期例如童工、学徒工或骇人听闻的工作场所安全问题那样的议题在21世纪的中国却缺位了。没有理由去相信党的仁慈会去对这一势头加以阻止并且减轻这些基本的劳动缺陷,更别提去看到党彻底地执行那些已经写在书上的最低工资或最长工作时间的法律。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是当今的自由放任市场,只有很有限的外部约束能去影响工作场所的工作条件——官员们竞相去避免环境上的灾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在相当多地方市场会影响到工资即便是在工人运动缺位的情况下。然而,中国劳动力的规模,在一个中或长的时间范围中打破了一种预测 “兴起的浪潮托起了所有船只”(“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景象的经济模型。采矿业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或是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例如截肢那样的严重工伤事故,已经让不少有潜力的工人选择退出该领域的劳动力市场并且远离危险的工作。对一小部分有技术的工人而言快速爬上生产阶梯以及从最危险的雇主处转向更有"信誉的"国内雇主甚至符合国际标准.外资企业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少数工人的荣景与大多数工人挣扎在生存线上这之间差距的快速上升只刺激了不满意以及被抛弃这样的情绪并且因此形成了动乱。
总体上缺乏对于中国的自由放任市场力量的外部约束导致了所谓的“中国价格”(“China price”)。一个更为灵敏的反应工人要求的政府可以强加一些管制——例如,去为在一家塑料工厂中(使其工人)暴露在有毒化学气体中施加限制,去为国家的雇员要求更多适当金额的赔偿,或去为工资强行制定标准——那会给(低廉的)中国(制造品的)价格施加压力。但是这个领导层再次在继续走当前这种“改革”路径的态度上意见一致。如果党致力于解决不平等或正在恶化的保障措施能被及时地加以改善,那么也许动乱的范围会缓和下来,但是中国价格会在吸引新投资上变得不太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增长的速度会被拉下来并且党和人民之间以“繁荣”来交换“稳定”的讨价还价可能会被大部分中国人所质疑。相对于由 “改革”落在后面的人士以慢慢发火的方式所形成的动乱,党可能判断繁荣之后所观察到的颓势对其统治是有有着更大威胁的。
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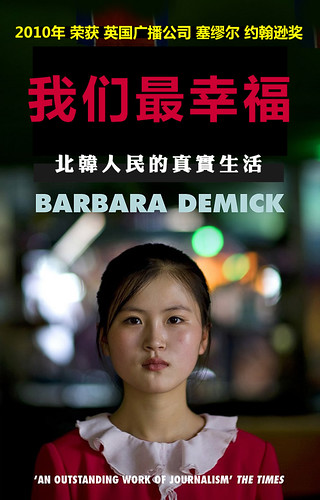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