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文安博士(Dr. Anne F. Thurston),目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Johns Hopkins SAIS)中国研究高级研究教授;草根中国计划主任,曾对《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英译版进行了近乎重写般的增删润色。
本文是作者参加2006年2月3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所举办的Hearing on Major Intern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听证会)Panel 4: Chinese Control Mechanisms 上的公开发言。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原文下载,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6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6_02_02wrts/06_02_02_thurston.pdf
开始我想要感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邀请我今天来这里作为你们今天所举行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领导层当前所面对的主要挑战”(major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听证会的一部分。
我一直坚信你们今天对我的邀请不是一个错误,你们真的很想听一下我在“另一个中国”的存在对中国领导层提出了什么挑战以及这些挑战会如何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上的看法。
我有时在与华盛顿的观众的谈话中会想起由已故的斯坦福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好些年前提到的一个告诫,这是个重要的并具有挑战性的告诫,他称之为“正确的认识中国”(“getting China right”),他说,“正确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具有致命性质的严重的问题”。
在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的岁月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书就是由艾萨克斯·哈罗德(Isaacs Harold)所著的《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在这部书中艾萨克斯详细叙述了美国在对待中国的看法上持续性的处于左右摇摆的极端状态。这类看法的转变一直都是从非常正面的,赞扬中国那悠久的历史以及伟大的文明,它那令人敬佩的勤劳、富有智慧的人民,到极为负面的认为中国是一个极为残暴、野蛮、不人道的国家.。而且艾萨克斯指出,不仅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来回摇摆像个钟摆,正反两面的意见往往也是同时存在的。
我仍然发现“正确的认识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太多样化了,并且让我们在理解它的所有复杂性时变动得太过于快速了。但是我在“另一个中国”上的经验导致我认为我们在观察“崛起的中国”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发生了,当我们把中国当成陈述句的主语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指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其他几个大型的、位于该国东海岸的繁荣的大城市。
我发现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胡鞍钢所做的,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分析是更为实用的。我会简单的把胡的分析放在这里讲给大家听一下。
像上海、北京以及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加上那些蓬勃发展的位于东部的沿海省份,通常构成了胡鞍钢分析里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这两个世界就是我们通常在谈论崛起中的中国时意味的对象。那是一个自1978年改革以来,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的中国,中国很可能超过了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变成了世界上第四大的经济体,那是一个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那是许多人视之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或至少是一个潜在的、寻求支配亚洲和世界霸权的中国。那是一个让一些美国人感觉到恐惧的中国。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中国拥有了3亿的人口。比美国的人口还要来得大。
还剩下的拥有着10亿人口规模的中国人民。这些人构成了胡鞍钢所谓的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那基本上就是我所说的另一个中国。
所以我想说一些关于另一个中国的事情。另一个中国最为根本的现实就是只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增长得更快了,所以它的收入不平等的比率也一直都在增长。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是经济学家用来测度不平等的一个指标,0代表绝对平等,1象征着绝对不平等,已经从改革进行时期的估计值0.28增长到了2004年的0.45左右。最近一份出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认为差距还要来得更高,基尼指数可能高达0.55。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水平比资本主义的美国还要来得大,美国的基尼指数为0.40。
另一个中国有着许多张面孔。另一个中国的成员大部分都生活在农村。贫富之间最根本的差距就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在最为贫穷的省份,富裕情况都要比农村地区好上很多。统计数字是令人震惊的。拥有4亿5千8百万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36%)的中国城市的人均收入是每年1033美元。拥有8亿7百万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64%)的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是每年319美元——比由世界银行所设定的贫困标准一天一美元还要来得低。公布于2005年年末中国最新的统计资料,提供的数字显示67%的农村人口,大约5亿4千万的人,每天赚的钱都不到一美元。中国农民每年的平均支出只有236美元——0.65美元一天。
如果这个“另一个中国”是一个国家,它将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这个乡村的,别样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太多人口、太少土地以及不太足够水源的农村地区,在那里税是高的,官员是腐败的,并且许多父母无法供应他们的子女去上学,在那里卫生体系已经走向末路,大约80%的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失去健康是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灾难性疫情威胁无处不在。禽流感只是最为近期才让人感觉到恐惧的隐忧。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已修改了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影响的人数,从估计为840,000 人下降到了大约为 650,000人。尽管如此,但是大家都同意问题是尖锐的。我假设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所提警告仍然是成立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已经说中国“现在正在见证令人难以置信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传染病情的显现……濒临一场灾难,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人间浩劫、经济损失和社会破坏。
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是另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大多居住在遥远的大西部的贫困的农村地区。中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的8.4%,但他们却构成了官方所承认的贫困人口的40%,并且遭受到了额外的明目张胆的负担,有时则是恶意的歧视。
许多妇女同样落在了另一中国的分类中。当男女比例继续失调,男性人口每年的出生率要远远超过同期的女性人口出生率。农村地区的妇女尤其是不能幸免的。中国的妇女构成了世界上女性人口的大约20%,但由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统计却发现,大约56%的女性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而中国女性自杀事件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
然而另一个中国不再只是广袤的农村地区。有着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弱势人群的城市中国也被包括其中。城市里面被包括在另一个中国的人口中最为大量的就是外来人口,1亿4千万到2亿的外来务工者为了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农村。每个主要的中国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规模巨大的、为农村外来人口所占据的飞地(enclave),在那里数万人挤住在拥有次等的住房条件、最低水平卫生系统的贫民窟里。受到了他们所服务的城市居民的隔离(isolated)以及虐待(ill-treated)。外来打工者做苦力(这个汉字名词来源于英语“coolie”),代表城市居民做痛苦的劳力活。他们是修建了供大量城市居民居住和工作的新摩天大楼以及公寓楼的建筑工人。这些人是蓬勃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无数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在那里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准低,工厂管理层不对安全问题关心,这种情形保证了西方国家明显地拥有了一个能够无限供给廉价制成品的制造基地。
另一个中国还包括了一个越来越多的街道儿童群体,他们被身在农村的父母送到城市去自食其力,因为那些父母太贫穷了以至于无法养活他们。
并且中国城市的贫困局面也是自发的(不完全是由外来打工人口的迁入而造成的)。数千万的城市工人,从衰败的国有企业下岗的,并且通常都没有得到一个安全网照顾的,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市贫民。有大约2500万退休居民没有退休养老金,每天开支不到一美元生活在贫困状态中。当数千万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居民开始要退休的时候,在2020年以后这类人群的人数可能会增长。除非激进的改革很快就能得到执行,否则许多中国城市中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居民将不会拥有退休金或获得医疗保健。.
我还会再加上一类人,那就是千百万中国的城市中的被拆迁户,他们的住宅为了空出去修建新摩天大楼以及公寓楼而被推倒了,并且摧毁他们的家园所给予的补偿不可能充裕到再购买一处令他们感觉到满意的新住宅。在农村地区,7,000万的中国农民已经在近些年中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今天中国各处,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正看到开发商以及官员勾结在一起从普通公民手里以“社会进步”的利益为幌子来掠夺土地以及住宅。这类土地以及住宅的攫取是今天我们在中国许多地方所看到的抗议事件产生的一个主要肇因。
降临到另一个中国头上的问题是巨大的。我并没认为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分开来看,另一个中国的问题可能形成挑战,但最终会被解决。合在一起看那些问题,中国正在直面的系列问题,其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都从未出现过。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是下一个十五年到二十年中国的领导层会集中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他们也必须那样去做。如果中国没有找到那样的意志、创造力以及资源去解决那些问题,它所面临的前景远不是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会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不能为它人民中相当多数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物品。我不认为这样的前景会发生。但中国——身在另一个中国中的人民,前途将非常坎坷。
大家都知道,中国正面临着一股日益高涨的不满之潮的冲击。我与谭睦瑞(Scott Tanner)质疑抗议活动的数量以及细节有所不同。然而在这里,让我简单说明来自中国公安部所公布的数字,这个数字指出了显著的抗议事故的不断增长。这类事故的数量从2004年的74,000起上升到了2005年的87,000起。如果相同比例的美国人口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去,(在美国)我们可能每年会遭遇到超过20,000起的抗议事件(平均下来每天发生55起大型的事故)。那是数量非常大的抗议活动。我不确信我们会如何或如何很好地处理这些事件。
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并理解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正在面对这些系列问题的考验,我们会回到米歇尔·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说的 “正确的认识中国”那样的立场上。我想中国政府确实认识到了症结所在,但它总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它看到这股不断兴起的不满之潮可能会危及到它的合法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见的是一个强大的、正在崛起的中国,害怕这个国家终有一天会威胁到我们。但是中国领导层看到的却是不断增长的国内的愤怒情绪并担心它们威胁其保持权力的能量。
我想我们也都会同意中国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所会带来的一个后果已经体现在了人权被侵犯的发生率已处于增长状态这样一种态势中。我们都看到了具有高尚理想以及良好意图的、有勇气的人士继续在遭受逮捕、骚扰以及迫害。我在这里只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陈光诚,这个双目失明的、自我成材的维权活动人士,在领导了一场反对山东省所实施的堕胎和绝育政策的司法运动——指控地方官员不遵守中国法律的行为,反对强迫妇女进行这种手术,在这场维权活动之后于2005年秋天成了报纸报道的头条。甚至在中央政府同意去调查陈光城所抗议的极端滥用权力的行为之后,陈光城仍遭到了地方当局的软禁和殴打。
还有吕邦列,一位来自湖北枝江市宝月寺村的34岁的农民,成了一个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并且在他领导了一次成功控告经选举产生但却不合法的进行贪污活动的村委会主任之后被共产党创办的中国青年报赞誉为“农村草根民主的先锋战士”。在跑到中国另一个村子——广东太石村(在那里农民当时正在寻求类似于发生在宝月寺村的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行动)施以援手之后,吕被那些明显受到雇佣的流氓打昏在地。今天,无论吕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公安流氓的跟踪。
还有律师GAOZHISHENG,他获得了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律师之一的声誉——受到了地下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的被拆迁户、民运人士、被剥削的煤矿工人和反对贪官的人士,被非法没收土地的人士、发生医疗事故的人士与被警察虐待的人士的支持。在他没有登记他的办公室地址变更之后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今天,他和他的家人都在不断被跟踪、被围困。
在中国政府对待这些有勇气的活动人士上我们必须继续表示我们的警告。但不幸的是,没有理由惊讶于中国政府会参与、允许或宽恕那些人权被侵犯的犯罪举动。
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越来越多的拒绝威胁、由使命感驱动的人士正在涌现出来,那些人正在坚持不懈地工作,即使面对恶意放置在他们前面的障碍。今天最使我感到振奋的是中国面对的每一个问题,人们都开始想要去解决它们。那些人我会把他们冠上“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的称号——他们是有使命感的人士,是对一个更好的中国有着愿景(vision)的人士,是不会停下来、不会放弃他们追求的人士。他们是已经看到了其所处社会问题的人士并且拒绝移开他们的目光,他们坚持借用来自哈维尔(Vaclav Havel)的思想——“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他们的使命是想要改变中国。他们不会用“不”来作为一个回答,直到他们的工作完成之后他们才会停歇下来。
中国一些最早期的社会企业家是在体制内推动改革的政府官员。直到非常近期为止,政府服务既是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又是最有可能推动积极改变的支点。有些社会企业家是学者。我认为中国社科院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博士已经观察到了广泛的农村不满现象并且号召他的知识分子同仁去帮助组织农民好让这样的组织更好的代表他们的利益。有些社会企业家是律师。有些则是与爱滋病患者,与最容易受到伤害、接触到爱滋病、被视为可耻群体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合作。有些社会企业家是中国偏僻地区的英语教师,有些则是先前的政府官员。
中国今天正在目睹这些社会企业家决心去变迁他们所处的部分世界以带来积极的改变那类举动真正的包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的社会企业家所受到的公众关注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社会企业家的人数在上万人,也许是几十万人之间并且这些人位于范围宽广的政治光谱之上。他们所做的大多数工作大多没有得到公众的喝彩但却通常会获得巨大成功。参加这次会议的谈话人被要求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拿今日中国的氛围与毛、邓、江时期的氛围做比较。社会企业家不太可能生活在毛、邓统治下的中国。假如生活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会被投进监狱。
我认为这些新的社会企业家的出现是重要的,基于以下若干理由。
第一,无论什么原因——在创新方面无法胜任(incompetence)也好,无兴趣(indifference)
也好,无力(inability)也好或在意志方面表现失败——中国政府不会尽快拿出解决之道去解决国家所面对的迫切问题。而政府口惠而实不至地去处理这些问题——持续的贫困以及越来越高的贫富差距,在基层政府层级上异乎寻常的腐败现象,一个遭到挑战的教育体制,一个失败的卫生服务系统,潜在的灾难性的传染病、环境灾难以及广泛的社会骚动——看起来他们是不愿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企业家对于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这些新的社会企业家正在成立旨在解决这些急迫问题的非政府组织 (NGO)。在另一个中国之中最令人兴奋的新发展就是由社会企业家所建立起来的数量急剧增长的非政府组织。自梁丛诫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已经十年多过去了。现在“公民组织”(或公民社会组织或通常被称作为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成千上万。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最近尝试一项对中国的各类组织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的计划,通过该计划他总结出中国现在拥有总数超过800万的登记注册或没有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准政府组织。这类组织的绝大部分,超过500万是得到了准政府的大型组织的支持,譬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
但中国现在是有着成千上万真正的非政府组织。随着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 在2005年10月访问中国之后,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当前拥有30万到70万 “提供着从司法援助到环境保护以及在乡村一级为儿童兴建游乐场所以及与农民分享小型农业的技术” 的公民社会组织。无论多么的犹豫,无论这样的进程来得多么的迟,中国正在加入到由Lester Salamon(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在1994年所宣布的“结社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的进程中来。
第三,这些新的非政府组织正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基础。公民社会的发展是重要的,因为,依我来看,如果中国讲开始成功地向一个更为开发、民主的方向转变一个稳固的公民社会对那样的前途是至关紧要的。中国当前的威权主义政府与一个更为民主化的未来中国之间最短的距离就需要一个公民社会的发展。
许多这样的新兴社会企业家以及这些新的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府来说犹如针芒在背。社会企业家们也不想形成这种局面,但他们却不得不那样。他们要求官员们遵守法律,他们在公民的合法权利上给公民们提供建议。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具备更大的透明度以及问责制,并且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以及支持者,他们也在提供别样的领导模式给他们,尤其是在地方层级上。地方官员,依我
个人经历来讲,被很普遍的认为是既腐败又对贫穷人士的苦难或对普通人的问题漠不关心的。人们这样告诉我,没有人会对地方政府保持相当的信任。中国的许多新兴社会企业家成了作为良好的地方领导人的典型。
第四,中国的新兴企业家以及由他们所运行的组织正在合作着,跨越一直以来很难去打破的障碍。
有些城市的知识分子已经在给那些弱势的农村社会提供援助。人权律师代表那些来自这个国家中越来越多样化的部分人群的客户。吕邦列则试图把他成功的例子在这个国家中从一处传递到另外一处。
并且拥有着共同目标的团体越来越聚拢到一起去向政府请愿。在2005年8月份,通过发布他们自己所做的对计划兴建的怒江水坝所会造成的环境影响的报告,61个非政府组织以及99名个人签署了一封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它自己的法律。计划兴建的怒江水坝会是非常大型的水坝工程,许多人都在担心它在技术上的可行性,担心它对兴建水坝所在地——一个生态上很丰富的地区所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居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有49个人已经签署了一份批评政府在东洲乡所进行的行为,在东洲乡村民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去抗议一个风力电厂的施工并且警察向抗议群众开了枪,造成了大约有20人死亡。有30个人签署了抗议太石村事件的公开信,在太石村,维权活动人士杨茂DONG(郭飞XIONG)被逮捕,吕邦列遭到了毒打。记者们已经签署请愿信抗议当局施压开除其编辑人员(新京报主编遭开除事件)。
中国的新兴社会企业家以及不断增长的非政府组织给中国政府出了道难题。这些人、这些团体都在致力于解决真正的问题,并且他们正在使用司法渠道去呼吁政府执行他们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中国的领导层不再坚持说,国家正面临到的巨大的系列问题是不存在的,政府也不再假装它自己就可以解决那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非政府组织被允许存在的原因。
我认为这就是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一个肇因。中国政府正偏执的关注国家陷入混乱的可能性。他们当然把这种兴起的社会不安现象看成是国家稳定局面遭到挑战的一种征兆。中国的新兴社会企业家以及新的非政府组织既是潜在的解决问题之道又是有可能导致那样的社会动乱的原因。他们一方面能帮助政府处理那些政府无法独自解决掉的问题,表现出他们可能会减少社会动乱的趋势。另一方面,那些政府无法独自解决掉的问题有一些是系统性的,并且必然会让一些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处于一个冲突状态。
今天中国处于中国社会最高层的领导者以及那些处于最低层的人士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在冲突正在发生的底层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贪污活动。贪污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提两点。
第一就是没有受到资金资助的授权统治活动,尤其在这个国家最为贫穷的地区。贫困地区的政府要负责诸如学校、道路以及地方人员薪水在内的各种公共品。当政府没有钱的时候,他们就向农民纳税,或对每个所能想象的活动以及财产进行强制收费。在许多地区,征收费和税已经变成了一种掠夺行为。
导致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所实施的财产权的本质所造成的。中国农民不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村庄的土地表面上都归集体所有。然而谁拥有分配土地的控制权,这些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土地权被出售是如何被解决的,以及谁从中获益是非常之模棱两可的。这种模棱两可性给勾结在一起的贪婪的地方官员以及贪婪的开发商带来了无限的贪污机会。
社会企业家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必然把他们自己放置在了一个会与地方当局产生冲突的位置上。并且当谈判解决冲突的做法失败,村民一下子转向抗议活动的时候,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就会冒被指控为“制造动乱”(“creating turmoil”)的风险,就像那些在1989年参加了抗议活动的学生所遭受到指控那样。
国际介入是一个另外的复杂情形。今天有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诸如扶贫、教育、卫生和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环境和司法改革这些议题上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多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都接受了国际支持,许多组织离开了这样的支持就无法再运作下去。许多外国非政府组织与一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关系非常紧密,中国政府肯定是一点也不满意于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不满的程度明显从去年春天的某个时期起得到了增长。
据我了解,这个问题始自俄罗斯对于近期所发生的、被称作是“颜色革命”的事件,尤其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所发生的“颜色革命”的观察,他们认为这些事件都显著的得到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中国显然也变得关注国际上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在中国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想要在中国去推动一次颜色革命。因此,政府开始了长达数月的、一系列的针对中国境内所有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我不知道有任何的外国非政府组织被中国政府拒绝让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阴影已经笼罩在了那些组织的头上,关于外国非政府组织新的规则以及条例仍然在被讨论。
如果要我们对中国政府说一句话,我们要说的是它的目标以及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目标之间没有什么巨大的冲突。中国政府已经把农村改革作为它最近的五年计划中的一项主要要去实现的目标。对农民所实行的农业税,被严厉批评要求加以废除。农村教育要实行免费。一个新的健康保险的体制要被引入到农村地区,致力于减少地方官员腐败的政策将会被促进。要去强调法治。并且在它近期公布的民主建设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宣称民主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共同要求并且许诺会继续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该白皮书提出的主要警告就是民主只是由内部产生出来,而非由外部力量强制输入而导致的。
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断裂长久以来已经变得非常之巨大了,在全国层级清楚表明的政策并不总是能在地方层级上得到实施,没有遭到由社会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弱势公民持续的推动以及刺激,惯性力量依然会作用下去。
很难言过其实的去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多么的重要。中国新兴的社会企业家以及由他们所运行的组织是中国的希望,是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改革的推动力。草根层面的变动就是来自这批人。如果民主要被引入那个国家,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就要依靠那些社会企业家以及那些由他们所运行的组织,他们所服务的那部分人群,在今天的中国以及一个可能在明天出现的民主中国之间必不可少的一项发展就是被大部分人称为公民社会的事物。许多新兴的社会企业家,通常意有所图地、有时候则是无意地,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努力。有些甚至是有意识的在推动民主。
我并不会以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言作为自己谈话的结尾。但这个研讨会已经要求各位发言人提出美国政府能做出什么主动行为(initiatives)或政策来帮助中国人民培育一个更为自由以及更具开放性的政治舞台。国内会导致改革的力量是来自这些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那些领导这些组织的社会企业家们。中国的这些供应变动的力量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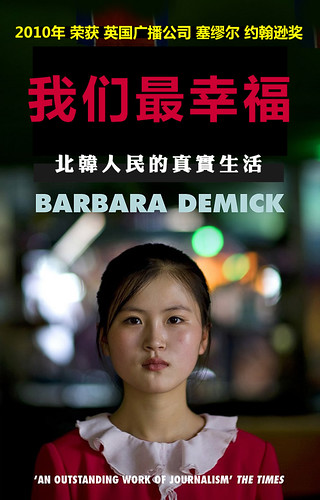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