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Obstacles to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来源:“五本书速成专家”网
作者:鲍瑞嘉(Richard Baum)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21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鲍瑞嘉的推荐:
裴敏欣:《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
杨大力:《再创中国》
蔡欣怡:《没有民主化的资本主义》
陈桂棣/吴春桃 《中国农民调查》
潘公凯:《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另外,RFI的“法国舆论看中国”有一期Podcast也选读了这篇书评的一部分,可以点击
鲍瑞嘉谈中国政治改革的障碍
收听,右键单击这里下载
UCLA的中国问题专家鲍瑞嘉认为,有些时候,中国的技术官僚们能够及时调整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这种能力让他感到由衷的敬佩;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又不得不对那种普遍的政治不安全感和党领导们固执地占有权力而摇头叹息。他选择了以下五本书来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障碍。
 第一本:中国的转型困局:专制主义发展的局限性 作者:裴敏欣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By Minxin Pei
第一本:中国的转型困局:专制主义发展的局限性 作者:裴敏欣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By Minxin Pei“您是否想从裴敏欣的《中国的转型困境》开始谈谈呢?在这本书的封底,有这样一则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sabeth Perry)所做的评论,‘这本书直接挑战了对中国崛起的一些传统想法……’”
裴敏欣的这本书很重要,因为他以最直接的方式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其核心就是中国是否能在创业革命中还保持其政治制度不受影响。裴敏欣的观点,简言之就是,列宁主义式政党是共产主义的原罪—在透明度和治理可靠性上存在着先天缺陷。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也引起了争议。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制造的自我认定的政治权力垄断事实上创造了一个封闭的集权社会。而这种社会形态,正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观察到的那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总是会变得极为腐败,因为缺乏制衡的力量。裴敏欣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无法克服其专制本质,阴谋化的起源,也就是它的“原罪”。而这会让党高度怀疑同时发生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活动,尤其是当这些活动被组织起来的时候。结果是,中国经济改革没能催生市场民主,而是成为了由国家主导的官僚资本主义,私人部门成为了党国集权者的附属。
按照裴敏欣的说法,中国于是陷入了“转型困局”。虽然其领导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受控的市场竞争采取了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个国家仍然陷于一种列宁主义的古老的政治框架中,无法自拔。最后他的结论是,党想要保持垄断性的政治权力的执着和日益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而这会让中国的领导人最终面临某种体制瘫痪,或/和痛苦的权力更迭。
 第二本:再创中国 作者:杨大力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By Dali Yang
第二本:再创中国 作者:杨大力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By Dali Yang本书列入您推荐的书单,是否暗示着您认同裴敏欣的看法?那么对于基本上完全与裴对立的杨大力的《再创中国》是您挑选的第二本书,您又有什么看法呢
虽然我的确同意裴敏欣的多数分析,他的书可以算是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稳定性的两极化观点中的其中一极。另外一极就是杨大力的《再创中国》,可以说是同等有说服力,也同样有争议。往好里说,杨大力认为裴敏欣所担心的极度腐败和中国的列宁主义政治形态有所夸大;往坏里说,则是完全错误。他的观点显然也有其价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逐渐产生的发展压力的时候,已经体现出了一种能够适应,调整和创新的积极能力。他认为中国的威权政体已经随着时间变得更有调适性,对社会的需要也更为关注。
举例来说,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中国长期停滞的、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非常抵制市场化改革,他们被强迫重组和兼并。成千上万的低效率的公司被推向破产,而那些保留下来的则被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以利润为导向的控股公司。结果是,产业效率和生产率都大幅提升了。
另一个例子则是政府对于逐渐增长的农村抗议的反应。当几个省的农民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抗议由当地农村官员强行征收的高额的、经常是非法的税收、费用和临时税之后,中央政府介入了,减轻了农民负担,取消了农业税,并设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征税限制。
最后一个例子,在中国沿海城市超时工作的农民工经常被拖欠工资,在几年前这引起了劳工动乱的浪潮,政府的应对方式是通过了新的劳动法,保障工会的代表性,确定了一周6天工作制,合强制的加班薪酬。这些例子说明虽然共产党是一个垄断的、没有竞争的政党,但是它却体现出令人敬佩的技术性管理能力,可以有效的应对逐渐深化的社会压力,并积极地微调国家的管理方式和规定。正是这种自我纠错和规则的调适性激发了杨大力对中国采取总体来说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在一党统治之下中国政治发展的能力。尽管这些都是在缺乏重大的民主化改革的前提下进行的。
那么谁是对的呢?裴敏欣还是杨大力?
这就是最难的问题了。我个人的回答摇摆不定。有的时候,我真的对中国的技术官僚领导体现出的与时俱进的能力表示由衷的钦佩,他们能够采取社会的经济的和环境的政策来应对严重的中国经济不均衡,为那些时运不济的,没有什么优势的社会成员提供补偿。在这些时候,我觉得我和杨大力的一些乐观看法是一致的。而另外一些时候,我又对那种无所不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和中国的党领导们对权力的固执占有摇头叹息,他们对于那种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反应过激,把他们逮捕、监禁。中国的领导人体现出一种很强烈的我称之为“后天安门紧张紊乱症”的症状:对那种即时的,未经授权举行的政治活动表现出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这种恐惧会激发他们最糟糕的政治本能,这又让我更倾向于裴敏欣对中国政治前景的悲观看法。
 第三本 蔡欣怡:《没有民主化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Kellee Tsai
第三本 蔡欣怡:《没有民主化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Kellee Tsai那么你推荐的其他书又如何看这一问题呢?
如果说裴敏欣和杨大力的辩论是比较宏观的话,我选择的其他的书是中更聚焦于某些具体的方面。可能不为人知,但是却为当代的中国政治的现状提供了更多线索。蔡欣怡(Kellee Tsai)的《没有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关注的是富裕的私人企业家阶层。当他们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崛起的时候,这些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表现出对西方式民主的真正兴趣,这可能和一些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有所矛盾。
那么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如何预测的呢?
最著名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给出的现代化理论预测说,当富裕、自信的城市商人和工业资产阶级涌现出来时,会对传统的、非常保守基础上的乡村贵族形成挑战,形成民主化的强劲动力。正如那句著名的摩尔语录所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化。”
要讨论摩尔的预言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成真,蔡注意到党国已经成功地和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合作,让他们爱国。他们为企业家们提供了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和机遇的特别优待,政府事实上收买了中国的私人部门对党国的忠诚。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家们不愿意得罪他们的金主,他们看起来对于中国现存的体制安排很满意。而且为什么不呢?他们一直是最大的受益者。蔡记录了党国体制成功的引诱和收买了私人部门,她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有关资产阶级不热衷于民主政治制度的解释。
这和裴敏欣及杨大力之间的争论有什么关联呢?
这是看待同一问题的另一角度。裴敏欣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是反历史的。也就是说它寻求的是不惜任何代价保护经济发展,这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压力。而杨大力则相反,“好吧。但是中国已经在发展中变得非常有活力,创造了一个更有适应性的、有对策的新版本的威权体制,而它事实上也有效果,也不一定会走向民主化的未来。”现在,在蔡提供的资料中,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包括狄忠蒲(Bruce Dickson)和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仔细地研究了中国新兴资产阶层的态度和价值观。他们认为裴敏欣对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民主化的信心是错误的。而他们的论述十分有说服力:因为正是共产党本身在指引经济的国有部门改革,它能够一手控制私人部门的生存、竞争和利润。只有那些与政府合作的企业家才有机会能够在新经济当中获利。结果就形成了政府权力和私有财富之间的联姻。如果你没有适当的官僚人脉、获得内部消息的话,你就不能在中国经济中获得成功。在这里蔡帮助解释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令人不解的调适性,而同时期其他的列宁主义政权都突然消失了。她很好地补充了杨大力对于中国政权可见的弹性的解释,而不是另作阐述。合并起来看,这两种现象—私人部门与政府的合作和政权的调整—都是中国共产主义出人意料的长存的原因。
那么企业家们支持政治制度是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它使自己受益。是这样的吗?
是的,这就是“能相处就继续”("Get Along, Go Along")的思路。比如说,成功的商人们得到了这样的诱惑,可以参与到党主导的咨询机构中,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或者他们因可以进入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而备受鼓励。通过收买而不是威胁,成功的企业家们就被织入了党国的网络,这创造了强大的发散的网络,政权和资产阶级之间获得了相互的支持。
我知道有好几位中国的企业家们被关进了监狱……
是的,但是只有当情况不妙的时候,失去控制的时候。通常来说,这个体系会保护自己。但是,当事情开始不可收拾,比如重大的贪污丑闻已经不能再被掩盖,需要作出一些牺牲的时候,某些坏人必须受到惩罚来平息众怒。但是这些通常都是偶然发生的个别案例;正如裴敏欣所说,体制缺陷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但是党国官员和商业经营之间形成的赞助商-客户关系总体来说是免于被清洗的。要想根除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体制转轨,党国担心这会造成不稳定,失去权力,也就没有动力作出这样的调整。因此裴敏欣将其称之为“转型困局”。
现在,私营财富和公共权力之间的联盟更加紧密了,这为党国和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是这桩交易中也有重大的输家—中国无法发声的农民和农民工。这些人是廉价劳动力,缺乏基本的福利保障,是他们支撑了中国经济从1980年代以来令人称奇的出口增长。虽然蔡很清楚地知道这种快速发展的受害者们被压抑的悲惨情况,这样的合谋式的发展对政权合法性制造了潜伏的挑战,但她本人并不担心这种潜力会如何削弱中国的威权体制党国的稳定性。
那么蔡最终是站在哪一边?
总体来说,她的分析是改革后的中国形成了政府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联盟,这补充了杨大力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上一条独特的通向威权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有效地绕过了民主改革。但是她意识到了中国的失利者和胜利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鸿沟,并且展示出一种本能的警惕,这一点上她更象裴敏欣,而不是杨大力。那么,和我一样,她看起来犹豫不决,在悲观和乐观的两极之间摇摆。
 第四本 陈桂棣/吴春桃 《中国农民调查》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 The Life of China’s Peasants By Chen Guide and Wu Chundao
第四本 陈桂棣/吴春桃 《中国农民调查》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 The Life of China’s Peasants By Chen Guide and Wu Chundao您列出的书单上的下一本书是关于农民的,《水能覆舟?》(中文版书名《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是陈桂棣和吴春桃。
裴敏欣、杨大力和蔡欣怡都注意到了,中国的底层民众长期以来都在斗争,希望分享经济改革带来的物质财富。陈桂棣和吴春桃则完全聚焦于农民的疾苦。他们的调查基本上抵销了最近政府为了改善农民福利的评价,陈和吴是中国本土的调查记者,他们展现的是悲惨的当代农村的现状。在2003年本书中文版出版之后很快就被禁,但是最终还是通过地下渠道销售了近1,000万本。最近这本书被翻成了英文。这是一系列的调查报告,记录了无情的村官如何和当地的企业家勾结起来,利用他们所有的权力和资源胁迫、恐吓农民,如何横行霸道。
作者认为中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是通过在改革之后,农民持续地承受长期不平等的,偏向城市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实现的。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程度比未经官方认可的基尼系数体现出来的还要高。[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的指数。]按照最近的估计,如果中国官员和他们的企业赞助商们在合法收入上,再加上从腐败中获得的个人所得的话,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最为腐败的非洲和拉美。在这个方面,陈和吴的书是对中国如此成功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总体GDP增长的警示,这种增长是以农村的广大贫民为代价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陈和吴的书,对那些把中国的城市经济奇迹描绘得太美好,却忽视了农村的阴暗面的观察者来说,这是一本可以矫正其观点的书。
那么陈和吴是否谈到了农民会威胁到政权呢?
虽然他们为持续的农村贫困、腐败和剥削描绘出了悲惨的图景,他们并没有特别指出这种功能失调会造成的潜在的政治后果。他们是记者,不是政治评论员。不过,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隐喻,不断增长的农村不满是中国统治阶层主要的焦虑来源。讽刺的是,正是这种焦虑让政府在最近一段时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也就是杨大力提到的那些——包括取消强制农业税,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为农民工提供劳动保护,和可承受的农村医疗保障。
党的领导人们对于农村骚动的担忧时常被公之于众。例如,2004年,胡锦涛主席公开承认“党的管理能力”存在严重的危机。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严肃对待这些危机,我们会发现自己被历史抛弃”。从那个时候开始,抗议示威和“群体性事件”事实上已经以每年20%的比例在增长。在2008年,也是最后一次公布这一数据的那年,全国发生了12万起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平均每天近350起。
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抗议呢?
这些大部分都是本地的抗议,针对的是不受约束的当地企业和官僚强权人物。金钱和政治的联姻造成的主要问题是,对这些企业家是如何挣钱,又是如何以普通人民为代价的,政府和人民的看法不同。在2008年四川发生了严重地震之后,很多观察者们发现,成百上千的震区学校倒塌了,而附近的政府大楼却受损不大。一些居民开始质疑这些豆腐渣工程,认为承包商们贿赂了当地官员,造成了建筑质量低下。中央政府要求记者们停止报道这样的控诉,并命令所有的外国记者离开这一地区。然后,当地政府开始骚扰那些对工程质量和腐败官员提出异议的公民,并拘禁甚至逮捕那些同意代表这些公民起诉的律师。
您的意思是说即使国家希望解决,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
从相当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国家似乎已经成为了它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的受害者——它已经创造了庞大的合作网路,他们互相支撑,如果真的要惩治腐败分子,和他们的客户方的根本利益,这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让整个体系垮塌。这时候我同意裴敏欣所说的转型的困境,改革党也会完蛋,不改党也会完蛋。
不过政府不是一直都在开展反腐运动……
是的,但是这些运动既不是持续的,也不是体制化的。他们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坏人,只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目的是将那些不符合道德的贪婪的个别官员揪出来示众,而不是以体制的、系统的方式来应对腐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提倡儒家的复兴。重新拥抱所谓的“仁慈的威权主义”可以提振民意,重新能够获得道德的支持,创建“和谐社会”,而不需要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因为是个人,而不是体制,成了不道德行为的根源,那么就没有必要改革整个体制。
在《水能覆舟?》一书中,农业们是否的确要求民主和政治改革了呢?
没有,他们既没有这样的信息,也没有这种诉求,也没有能力组织起来要求政治改革。有趣的是政府有意识地利用了大多数农民反抗的是当地党领导,这些人仅仅是政府的一部分,当地的警察头子是腐败的,或者某个工厂行贿了当地官员,让村里的饮用水受到了污染,这些怒火主要都集中在当地政府上,而不是如何让这些发生的整个体制。事实上政府鼓励这种意识,“不要怪我们,要怪就怪他们。”因此农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整个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他们可能知道他们受到了损失,但是不知道责任在哪一方,怎样才能停止。
当然,也缺乏横向的或者纵向的组织、专门的人员和利益团体把这些惨痛现状带给更广泛的手中,这可能会体现出某地农民与其他地方农民之间受到的屈辱的联系。党国非常注意防范这种跨地域的动员,跨地域的组织都成了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所有的利益团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才能够生存,他们的行动只能局限于本地。当大规模事件发生时,人们开始表达对当地政府的不满,中央政府就会介入进来收拾残局,通常是大把大把地撒钱,收买那些不满的群众。接着,一旦他们解除了抗议群体的大规模行动,他们就会悄悄地逮捕领导人,然后这些人就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这就是应对措施。因为没有了跨地域的组织者,就不能引起全国性的注意,一切都被局限在当地范围内。
不过,对历史上的大规模政治动荡来说,比如说,法国大革命,都有很多理由不会发生,但是还是发生了。
是的。在中国,我也看到了这种事可能发生的征兆,但是我的预测是不会出现大规模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我看到的是某种“公民社会”的雏形正在出现,挑战传统的“禁区”,和党国的威权主义特权。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和电子化的新媒体——手机、短信和互联网——携手前进。新媒体能够帮助被审查的信息自由流动,这是过去从来不可能做到的。
最近的一个令人惊叹的例子是重庆的“最牛钉子户”。这本来是一件屡见不鲜的事。当地政府和房地产发商合谋以低价格买下了城市地段,用于开发利润颇丰的高档住宅和商业区。因为是与当地政府联手,开发商提供微不足道的“拆迁补偿款”,让居民们搬离这一区域。过去的20年中,全国的地方政府都用类似手法进行所谓“土地征用”,驱逐居民,然后把土地租给商业地产商,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在最近一些年里,出现了抵制这种作法的公众不满。
这家重庆的钉子户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这户人家居住在规划中的重庆市中心的商业广场上,他们拒绝接受开发商提供的微不足道的补偿款搬离原来的住宅。他们要求更公平的补偿。在开发商带领当地流氓来强拆房屋的时候——如果你拒绝接受“被批准”的补偿款时这经常发生——这家居民开始用手机对建筑工地拍照,建筑公司已经在他家周围挖了很深的壕沟,“钉子户”的称呼就是因为它就像是被清空的工地上仅存的一座孤岛。开发商建起了很高的围栏避免其他人看到。但是人们通过手机上的相机打开了一条缝隙。他们在被占领的住所外挂上横幅,呼吁人们关注他们的困境。很快这就形成了“社会化网络”效应。人们开始以短信方式把这张图片传给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张贴这家“钉子户”的照片。很快这个故事象病毒一样传遍了全中国。
中国的官方媒体虽然压制新闻,很快就了解了这件事。这时中央政府向重庆派出“搞定麻烦者”,他则告诉地方政府:“听着,和这些人和解。这已经成了个麻烦事,而我们不想找麻烦。”于是他们命令市政府付给“钉子户”比原来的赔偿高出几倍了的拆迁补偿。
在此之后,中国的一些大胆的小报开始报导“钉子户传奇”,并称之为中国的“公民报道的诞生”。只有那些有手机和电脑的公民们才能够迫使政府后退。而最近这种事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这肯定让政府越来越担忧
 您列出的第五本是潘公凯的《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New China By Philip Pan
您列出的第五本是潘公凯的《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New China By Philip Pan这是一本和《水能覆舟?》类似的书。其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调查记者潘公凯,他描绘出几个中国腐败的受害者的生动画卷,潘也特别关注了一些勇敢的人,大部分是记者和律师,他们冒着自己职业的巨大风险,有时是生命危险,大胆揭穿当地官员和他们的下属所做的令人震惊的错事。如果说陈桂棣和吴春桃的案例研究完全是关于中国农村的话,潘公凯则选择了更广阔的当代中国视角,从手眼通天的房地产大亨,能够命令成百上千的北京居民为了2008年奥运会而拆迁,到中国东部的小镇恶棍,他们强迫当地妇女在妊娠晚期接受堕胎,好达到计划生育指标,再到勇敢的解放军军官,他揭开了政府掩盖着的沉默的大幕,说出了2003年中国北京的SARS流行真相。在这些典型人物中,潘公凯列出了后改革时期的中国典型的官员滥用权力的类别,并呼吁关注那一小群敢于揭露他们的恶行的真正的英雄。他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发展奇迹的阴暗面,同时也帮助我们重新点燃了对真正的尊严和人性的信念,正是在这些敢于与强权对抗的普通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
中国的年轻人,包括大学生们普遍对政治回避。他们说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他们这么说比较安全。如果所问的问题让人们觉得不便回答的话,多数人就学会了不再问。我之前注意到,党国在收买、合作等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如果其他手段都失效了的话,那么就体系化地恐吓反对者遵守他们的规矩。在1989年天安门悲剧之后,大多数的中国大学生退缩了,不再过问政治。后来,1992年,邓小平给他们开出了一个有策略的条件:“我们可以给你们从未想过的追求职业、高薪工作和其他好东西的机会;但是作为回报,你们不能再挑战党国或其领导人的权威。”大多数的中国学生接受了邓的条件,这不令人奇怪,他们也开始享受“能相处就继续”的思路。从那之后就少有学生运动了。
你对于中国的整体未来走势是什么感觉呢?
我也在前面所提的这些书中时常摇摆。有时我觉得裴敏欣是对的,有时我觉得杨大力是对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是没有先例的。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成功的、渐变的后列宁主义转型的例子。有许多激烈的反列宁主义的暴乱,也出现过亲列宁主义的回潮,但是其他没有任何地方是这样,在列宁主义的一党独裁下嫁接到持续的现代化和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例子。我真是不清楚这是否能成功。
我不想说得太悲观。也许中国的确有机会从中发展处一条不被西方人认可为民主制度的政治体系。也许一种更为仁慈的、亲善的新儒家式家长制可以调和列宁主义的铁拳,党国的权力独裁也就不必土崩瓦解。但是我对现在这种政治上的列宁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形成的腐败关系是否能长期运转表示怀疑。
译注
1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13-20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加,哈佛大学教授。摩尔对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有着强烈的影响,《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是他的成名之作。
看不到相关阅读?点击这里一键翻墙
相关阅读
- 安装适合你的浏览器的红杏插件一键翻墙
- 翻墙看《译者》https://yyii.org
-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订阅《译者》;
-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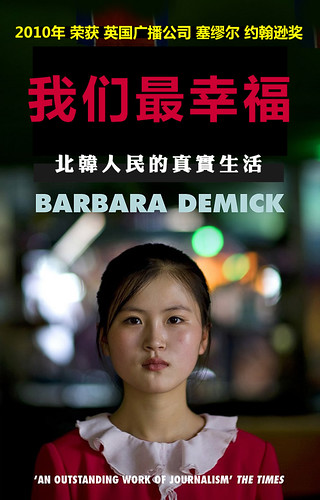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1 comments:
自上而下的改良在绝对专制的统治者中始终是空想,即使是知道患病,人贪婪的本性决定。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