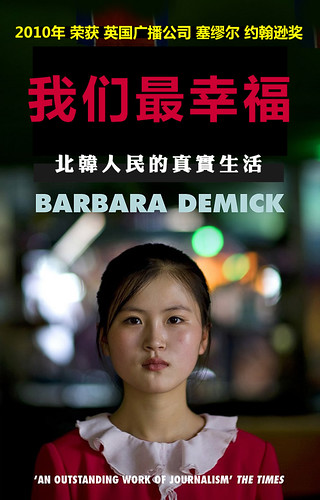核心提示:直到現在,認真想過中國政權過渡的概率和各種可能情況的人很少。
原文:5 Ways China Could Become a Democracy
作者:裴敏欣
日期:2013/02/13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同時參考同源譯文。

猜測中國可能的政治前途,是種會使一些人感到有趣味、許多人覺得困惑的智力活動。傳統觀點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共產黨想要捍衛及延續其政治壟斷之心如此堅定,它有能力存活較長時間(儘管不是永遠)。但是,少數人的觀點則是中共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事實上,在未來10至15年中國向民主過渡是個大概率事件。在這種對中國民主前景的樂觀看法背後,是積累下來有關民主過渡的國際及歷史經驗(過去40年,大約有80個國家完成了從專制統治過渡至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民主體制);幾十年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經就民主過渡及專制制度的崩壞(兩個緊密關聯的過程)的動態形成了重要的見解。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認為中國的一黨政權仍然具有足夠的韌性去維持幾十年統治的人可以指出,共產黨擁有經過驗證的巨大鎮壓能力(專制政權生存的最關鍵因素),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的能力(儘管這適應力的程度在學術上有爭議)以及它合法性的來源:達致經濟改善的記錄。
至於為什麼中國人將擺脫幾十年一黨統治的一系列理據當中,那些認為中國政權更迭是可預見的人已經挑選出來一組因素。而在眾多的專制統治的衰落和崩潰的原因當中,兩個因素脫穎而出。
首先是專制政體衰變的理論。一黨政權,不論怎樣精密,還是會受到組織的老化和衰變的影響。領導者(在能力和意識形態方面) 逐漸衰弱;這種制度往往吸引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一些從投資者角度來看他們在政權內的角色的人,他們想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為維護政權出力所能得到的回報。結果是腐敗不斷加劇,管治持續惡化,與群眾日益疏遠。根據經驗,一黨制政體的組織衰變可以用這種政制的有限的壽命來測量。至目前為止,記錄上一黨政權的最長壽命是74年(前蘇聯共產黨)。在墨西哥和台灣的一黨政權分別掌權71年和73年(然而,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失敗使台灣的情況複雜些)。此外,這三個主政時間最長的一黨政權在退出政治權力的大約十年前便開始體驗到體制性的危機。如果相同的歷史在共產黨統治了63年的中國重複,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未來10到15年政權過渡的概率是有可能的—當中共達到一黨政權壽命上限的時候。
其次,社會經濟變革的影響。識字率,收入和城市化速度不斷提高,通信技術的改善等極大的降低了集體行動、瓦解獨裁統治合法性的成本,並促進更大的民主要求。其結果是,管治貧困農業社會得心應手的獨裁政權,發現一旦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要繼續統治越來越困難,最終變得不可能維持。統計分析表明,當人均收入上升到1000美元以上,獨裁政權便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更大)。當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民主轉型的可能性增加更為顯著。一旦人均收入達到6000美元,能夠生存的獨裁政權很少,除非他們統治的是石油生產國。如果對中國應用這種觀察,並且也考慮通脹的可能影響(儘管上述的人均收入數據是以常數來計算的),我們會發現,中國已經深入這個"民主過渡區域"了,現在它的人均收入是大約9,100美元,和1980年代中期民主過渡前夕的韓國和台灣的人均收入水平不相上下。再過10-1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會超過15,000元,城市化率將上升到60-65%。如果中國共產黨今天在部署的人力和財力資源來維持統治時覺得艱難,試想一下,10-15年後,這事情將會變得有多不可能做到。
如果這種分析有足夠的說服力,使我們願意設想未來10-15年間,中國很有可能出現的民主轉型的話,那麼更有趣的後續問題絕對是,"這樣的轉變會怎樣發生?"
同樣,根據70年代民主轉型的豐富經驗,自20世紀70年代,中國可能成為民主有五種方式:
"大團圓結局"將是中國民主過渡的最好模式。通常情況下,一個由舊政權的統治精英操作的和平權力退出會經過幾個階段。開始時,也許由於多種因素(如經濟表現不佳,軍事上的失敗,人民反抗升級,無法忍受的鎮壓成本,和貪污成風),政權出現合法性危機。對這種危機的承認/覺察使某些政權的領導的認為專制統治的日子屈指可數,他們應該開始操作一個不失體面的權力退出。如果這種領袖取得政權內部的政治優勢,他們會通過開放媒體和放鬆對民間社會的控制來啓動自由化的過程。然後,他們會與反對派領導人磋商從而設定後過渡期政治制度的規則。最關鍵的是,這些談判重心是保護舊政權那些曾侵犯人權的統治精英,和保留支持舊政權的國家機構(如軍隊和秘密警察)的特權。談判結束後,便會舉行大選。 在大多數情況下(台灣和西班牙例外),代表舊政權的政黨在這樣的選舉中落敗,從而迎來一個新的民主時代。目前,緬甸的過渡正在按照這個劇本上演。
但對中國而言,這種大團圓結局的的概率取決於執政精英能否在舊政權的合法性遭受無法挽回的損失之前著手改革。後極權主義政權和平過渡的往績非常糟糕,原因主要是這些政權一直抗拒改革,直至失去時機之後才著手。"大團圓"式轉變的成功案例—如在台灣,墨西哥,巴西發生的那些—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舊政權仍然保持足夠的政治力量和得到主要社會團體一定程度的支持。所以,統治精英越早開始這個過程,成功的機會越大。然而,弔詭的是,足夠強大的政權不願意改革,而虛弱的政權則無力改革。在中國的情況下,"軟著陸"的機會可能取決於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在未來五年會做的事。畢竟,政治軟著陸的機會之窗不會永遠保持開放。
"戈氏來到中國"是有著險惡情節的"大團圓結局"的變奏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層錯過歷史機遇,沒有在刻下啟動改革。但是,在未來十年內,經濟、社會和政治趨勢(如人口老化,環境惡化,裙帶資本主義,不平等,腐敗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動亂導致經濟增長不斷下 滑)最終會迫使政權面對現實。強硬派名譽掃地,取而代之的是像戈爾巴喬夫一樣的改革者,他們開展中國版的glasnost和perestroika(譯註:俄語,改革於開放)。 但屆時政權已經失去了重要社會群體的完全信任和政治上的支持。自由化引發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和極端主義。舊政權的成員開始叛逃—不是向反對派倒戈,便是跑到 他們在南加州或瑞士的避風港。在政局混亂之際,政權遭受又一次內部分裂,類似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之間的那樣,結果激進的民主化人士崛起,取代溫和的改革 者。憑藉巨大的民望,佔主導地位的政治反對派—包括許多舊政權的叛逃者—拒絕向實實在在沒有談判條件的共產黨讓步。黨的統治會崩潰,不是因為選舉結果引致忠於它的人下台,便會是反對派自發奪取政權造成。
假若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那將是最諷刺的事。在過去2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竭盡所能來避免蘇聯式的崩潰。如果"戈氏一幕"給中國帶來民主,那表示中共顯然的從前蘇聯解體吸取了錯誤的教訓。
"天安門終極版"是第三種可能性。當中共即使面對政治轉趨激進以及社會分化跡象,卻還是繼續抵制改革的時候,便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造成"中國的戈氏"的因素在這裡也會起作用。不過,觸發崩潰的不是體制內改革者遲來的自由化改革,而是像1989年天安門事件那樣,能夠廣泛動員全國各地眾多社會組織的一場不可預料的大規模起義。這種政治革命的表現形式將會和天安門民主運動以及中東"茉莉花革命" 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裡看到的一樣。在中國的情況下,"天安門終極版"產生了不同的政治成果,主要是因為中國軍方拒絕再次插手挽救中共(自1970年代以來大多數由危機引發的轉變當中,軍隊在最關鍵的時刻放棄了專制統治者)。
"金融危機"—第四個可能情況—可能會像1997至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導致印尼的蘇哈托倒台那樣啟動中國的民主轉型。中國那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與蘇哈托時代的印尼銀行系統有許多共通特性:政治化、任人唯親、貪污腐敗、監管不力以及風險管理能力較弱。眾所周知,今天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累積了巨額不良貸款,而如果這些貸款被確認的話,在技術上可能會破產。此外,最近幾年中通過影子銀行系統進行資產負債表上不記錄的活動如雨後春筍一樣,使金融穩定性面臨更大風險。隨著中國維持資本控制的能力因為資金進出中國的方式增加而受到削弱,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使事情變得更糟的是,中國不成熟的資本帳戶自由化措施有助資本在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時候外逃。如果中國的金融業遭受崩潰,經濟將陷於停頓,社會動盪將有可能變得無法控制。如果安全部隊未能恢復秩序,而軍方又拒絕幫助中共的話,中共有可能在混亂中失去權力。單獨由金融危機引起崩潰的概率是比較低的。但是,即使中共捱過金融危機的直接後果,中國付出的經濟代價將很有可能損害其經濟表現到一個足以產生連鎖效應,使中共最終失去法理權威的程度。
"環境崩潰"是最後一個可能導致政權更迭的情況。鑑於近日中國環境惡化的顯著程度,環境破壞引起政權更迭的概率並不少。連接環境破壞和政權更迭的反饋環路雖然複雜,但並非不可理解。顯然,環境崩潰造成的衛生保健問題、生產力喪失、水資源短缺和物理破壞等方面的經濟成本將是巨大的。增長可能會停滯,因而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和控制。環境崩潰已經開始使中國城鎮的中產階級對政權離心,並引發日益嚴重的社會抗議。環保行動可以成為一個政治力量,把不同社會群體連接在一起,為共同的事業向對環境問題不敏感、反應遲鈍、和不稱職的一黨政權抗爭。中國環境的嚴重退化也意味著發生環境大災難諸如大規模的有毒物質洩漏、創紀錄的乾旱、長時間的有毒煙霧等的機率可能引發大規模抗議事件,使反對派有機會迅𨒪政治動員。
這種智力練習的得著應該是發人深省的,不論對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社會都一樣。至目前為止,很少有人認真想過中國政權過渡的概率,以及各種可能的情況。思考這樣一個政權過渡的可能原因和情景之後,應該能了解有一點是再明顯不過的:我們得要開始思考不可想像的和無法避免的事情了。
原文:5 Ways China Could Become a Democracy
作者:裴敏欣
日期:2013/02/13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同時參考同源譯文。

猜測中國可能的政治前途,是種會使一些人感到有趣味、許多人覺得困惑的智力活動。傳統觀點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共產黨想要捍衛及延續其政治壟斷之心如此堅定,它有能力存活較長時間(儘管不是永遠)。但是,少數人的觀點則是中共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事實上,在未來10至15年中國向民主過渡是個大概率事件。在這種對中國民主前景的樂觀看法背後,是積累下來有關民主過渡的國際及歷史經驗(過去40年,大約有80個國家完成了從專制統治過渡至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民主體制);幾十年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經就民主過渡及專制制度的崩壞(兩個緊密關聯的過程)的動態形成了重要的見解。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認為中國的一黨政權仍然具有足夠的韌性去維持幾十年統治的人可以指出,共產黨擁有經過驗證的巨大鎮壓能力(專制政權生存的最關鍵因素),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的能力(儘管這適應力的程度在學術上有爭議)以及它合法性的來源:達致經濟改善的記錄。
至於為什麼中國人將擺脫幾十年一黨統治的一系列理據當中,那些認為中國政權更迭是可預見的人已經挑選出來一組因素。而在眾多的專制統治的衰落和崩潰的原因當中,兩個因素脫穎而出。
首先是專制政體衰變的理論。一黨政權,不論怎樣精密,還是會受到組織的老化和衰變的影響。領導者(在能力和意識形態方面) 逐漸衰弱;這種制度往往吸引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一些從投資者角度來看他們在政權內的角色的人,他們想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為維護政權出力所能得到的回報。結果是腐敗不斷加劇,管治持續惡化,與群眾日益疏遠。根據經驗,一黨制政體的組織衰變可以用這種政制的有限的壽命來測量。至目前為止,記錄上一黨政權的最長壽命是74年(前蘇聯共產黨)。在墨西哥和台灣的一黨政權分別掌權71年和73年(然而,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失敗使台灣的情況複雜些)。此外,這三個主政時間最長的一黨政權在退出政治權力的大約十年前便開始體驗到體制性的危機。如果相同的歷史在共產黨統治了63年的中國重複,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未來10到15年政權過渡的概率是有可能的—當中共達到一黨政權壽命上限的時候。
其次,社會經濟變革的影響。識字率,收入和城市化速度不斷提高,通信技術的改善等極大的降低了集體行動、瓦解獨裁統治合法性的成本,並促進更大的民主要求。其結果是,管治貧困農業社會得心應手的獨裁政權,發現一旦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要繼續統治越來越困難,最終變得不可能維持。統計分析表明,當人均收入上升到1000美元以上,獨裁政權便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更大)。當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民主轉型的可能性增加更為顯著。一旦人均收入達到6000美元,能夠生存的獨裁政權很少,除非他們統治的是石油生產國。如果對中國應用這種觀察,並且也考慮通脹的可能影響(儘管上述的人均收入數據是以常數來計算的),我們會發現,中國已經深入這個"民主過渡區域"了,現在它的人均收入是大約9,100美元,和1980年代中期民主過渡前夕的韓國和台灣的人均收入水平不相上下。再過10-1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會超過15,000元,城市化率將上升到60-65%。如果中國共產黨今天在部署的人力和財力資源來維持統治時覺得艱難,試想一下,10-15年後,這事情將會變得有多不可能做到。
如果這種分析有足夠的說服力,使我們願意設想未來10-15年間,中國很有可能出現的民主轉型的話,那麼更有趣的後續問題絕對是,"這樣的轉變會怎樣發生?"
同樣,根據70年代民主轉型的豐富經驗,自20世紀70年代,中國可能成為民主有五種方式:
"大團圓結局"將是中國民主過渡的最好模式。通常情況下,一個由舊政權的統治精英操作的和平權力退出會經過幾個階段。開始時,也許由於多種因素(如經濟表現不佳,軍事上的失敗,人民反抗升級,無法忍受的鎮壓成本,和貪污成風),政權出現合法性危機。對這種危機的承認/覺察使某些政權的領導的認為專制統治的日子屈指可數,他們應該開始操作一個不失體面的權力退出。如果這種領袖取得政權內部的政治優勢,他們會通過開放媒體和放鬆對民間社會的控制來啓動自由化的過程。然後,他們會與反對派領導人磋商從而設定後過渡期政治制度的規則。最關鍵的是,這些談判重心是保護舊政權那些曾侵犯人權的統治精英,和保留支持舊政權的國家機構(如軍隊和秘密警察)的特權。談判結束後,便會舉行大選。 在大多數情況下(台灣和西班牙例外),代表舊政權的政黨在這樣的選舉中落敗,從而迎來一個新的民主時代。目前,緬甸的過渡正在按照這個劇本上演。
但對中國而言,這種大團圓結局的的概率取決於執政精英能否在舊政權的合法性遭受無法挽回的損失之前著手改革。後極權主義政權和平過渡的往績非常糟糕,原因主要是這些政權一直抗拒改革,直至失去時機之後才著手。"大團圓"式轉變的成功案例—如在台灣,墨西哥,巴西發生的那些—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舊政權仍然保持足夠的政治力量和得到主要社會團體一定程度的支持。所以,統治精英越早開始這個過程,成功的機會越大。然而,弔詭的是,足夠強大的政權不願意改革,而虛弱的政權則無力改革。在中國的情況下,"軟著陸"的機會可能取決於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在未來五年會做的事。畢竟,政治軟著陸的機會之窗不會永遠保持開放。
"戈氏來到中國"是有著險惡情節的"大團圓結局"的變奏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層錯過歷史機遇,沒有在刻下啟動改革。但是,在未來十年內,經濟、社會和政治趨勢(如人口老化,環境惡化,裙帶資本主義,不平等,腐敗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動亂導致經濟增長不斷下 滑)最終會迫使政權面對現實。強硬派名譽掃地,取而代之的是像戈爾巴喬夫一樣的改革者,他們開展中國版的glasnost和perestroika(譯註:俄語,改革於開放)。 但屆時政權已經失去了重要社會群體的完全信任和政治上的支持。自由化引發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和極端主義。舊政權的成員開始叛逃—不是向反對派倒戈,便是跑到 他們在南加州或瑞士的避風港。在政局混亂之際,政權遭受又一次內部分裂,類似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之間的那樣,結果激進的民主化人士崛起,取代溫和的改革 者。憑藉巨大的民望,佔主導地位的政治反對派—包括許多舊政權的叛逃者—拒絕向實實在在沒有談判條件的共產黨讓步。黨的統治會崩潰,不是因為選舉結果引致忠於它的人下台,便會是反對派自發奪取政權造成。
假若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那將是最諷刺的事。在過去2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竭盡所能來避免蘇聯式的崩潰。如果"戈氏一幕"給中國帶來民主,那表示中共顯然的從前蘇聯解體吸取了錯誤的教訓。
"天安門終極版"是第三種可能性。當中共即使面對政治轉趨激進以及社會分化跡象,卻還是繼續抵制改革的時候,便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造成"中國的戈氏"的因素在這裡也會起作用。不過,觸發崩潰的不是體制內改革者遲來的自由化改革,而是像1989年天安門事件那樣,能夠廣泛動員全國各地眾多社會組織的一場不可預料的大規模起義。這種政治革命的表現形式將會和天安門民主運動以及中東"茉莉花革命" 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裡看到的一樣。在中國的情況下,"天安門終極版"產生了不同的政治成果,主要是因為中國軍方拒絕再次插手挽救中共(自1970年代以來大多數由危機引發的轉變當中,軍隊在最關鍵的時刻放棄了專制統治者)。
"金融危機"—第四個可能情況—可能會像1997至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導致印尼的蘇哈托倒台那樣啟動中國的民主轉型。中國那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與蘇哈托時代的印尼銀行系統有許多共通特性:政治化、任人唯親、貪污腐敗、監管不力以及風險管理能力較弱。眾所周知,今天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累積了巨額不良貸款,而如果這些貸款被確認的話,在技術上可能會破產。此外,最近幾年中通過影子銀行系統進行資產負債表上不記錄的活動如雨後春筍一樣,使金融穩定性面臨更大風險。隨著中國維持資本控制的能力因為資金進出中國的方式增加而受到削弱,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使事情變得更糟的是,中國不成熟的資本帳戶自由化措施有助資本在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時候外逃。如果中國的金融業遭受崩潰,經濟將陷於停頓,社會動盪將有可能變得無法控制。如果安全部隊未能恢復秩序,而軍方又拒絕幫助中共的話,中共有可能在混亂中失去權力。單獨由金融危機引起崩潰的概率是比較低的。但是,即使中共捱過金融危機的直接後果,中國付出的經濟代價將很有可能損害其經濟表現到一個足以產生連鎖效應,使中共最終失去法理權威的程度。
"環境崩潰"是最後一個可能導致政權更迭的情況。鑑於近日中國環境惡化的顯著程度,環境破壞引起政權更迭的概率並不少。連接環境破壞和政權更迭的反饋環路雖然複雜,但並非不可理解。顯然,環境崩潰造成的衛生保健問題、生產力喪失、水資源短缺和物理破壞等方面的經濟成本將是巨大的。增長可能會停滯,因而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和控制。環境崩潰已經開始使中國城鎮的中產階級對政權離心,並引發日益嚴重的社會抗議。環保行動可以成為一個政治力量,把不同社會群體連接在一起,為共同的事業向對環境問題不敏感、反應遲鈍、和不稱職的一黨政權抗爭。中國環境的嚴重退化也意味著發生環境大災難諸如大規模的有毒物質洩漏、創紀錄的乾旱、長時間的有毒煙霧等的機率可能引發大規模抗議事件,使反對派有機會迅𨒪政治動員。
這種智力練習的得著應該是發人深省的,不論對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社會都一樣。至目前為止,很少有人認真想過中國政權過渡的概率,以及各種可能的情況。思考這樣一個政權過渡的可能原因和情景之後,應該能了解有一點是再明顯不過的:我們得要開始思考不可想像的和無法避免的事情了。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