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天,我的未来老公 Bob 骑着自行车横穿中国来重庆看我 - 在我印象中他是第一个骑车横穿中国的美国人。作为一个还没出嫁女儿,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没结婚的人没法分到房子。我的父母40年代末都是地下党员,二战后的年月里积极地参加反美抗议活动。所以当一个老美扛着自行车爬了四层楼,走进我们家的单元门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那时候,在重庆这个内陆的山城,自行车和老外都很罕见。西方人才刚刚开始被谨慎地允许在国内四处走动 -前提是他们不违反这个国家那些经常看不见的各种规矩,也不到处追求我们纯洁的姑娘们。
我的父母仅仅出于他们的好客传统才暂时容忍了 Bob 在这里待上一天(我告诉父母Bob是我的研究生院老师)。第二天,爸爸就再也没法忍受他的不舒服,叫 Bob 走人。在下达逐客令之前,他建议Bob参观一下坐落在重庆西边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
“什么是中美合作所?”Bob问。他的问题让我吃惊。从没出过国的我以为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是SACO(“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就像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美合作所”。
我于是把那些从小学起就知道了的东西告诉 Bob:中美合作所是个美国人办的集中营,在四十年代折磨杀害地下党员。它有两处监狱,一处叫渣滓洞,另外一处叫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叫梅乐斯 (Milton Miles),美国海军军官,中方负责人是戴笠,国民党秘密特务机构(全称是军事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头子。我父母和他们的地下党同志们管戴笠叫"中国的希姆莱(纳粹党卫军头目)"。
Bob基本上不太关心政治,对我说的几乎没兴趣。他对“美国人办的集中营”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些杜撰而已。Bob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他在1987年来中国之前读过些关于中美历史的书,但从来没听说过这事。
尽管我并不想Bob去参观中美合作所,而且不喜欢我父亲试图给一个美国人灌输负罪感,Bob不屑一顾的态度还是让我很恼火。“这个是真的”,我说。在中美合作所旧址上的博物馆里,我见过标着“美国制造”的手铐,还有照片上戴着那些手铐的尸体。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的原因(实际上八十年代初我就因为些不同看法和文字在政治上惹过一些麻烦),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至少我是这么想。Bob 只耸耸肩,不相信也不想争辩。
后来回想起来,Bob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反驳大陆版中美合作所历史的人,尽管他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直觉(以及一点美国人的偏见)。他后来推测说,如果真有那么耸人听闻的美国在中国办的集中营,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能获普利策奖的报道机会,而那样的话中美合作所在美国就应该变得众人皆知才对。
但是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直接了当。
***
下面这些在中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 在政权交替之际,在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座步行距离之内的监狱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那天遇难的有超过200人。在白公馆,处决是分批进行的,直到晚上都还没怎么结束,也就是那时还活着的二十个狱友在一个同情他们的看守的帮助下逃走了。在渣滓洞,狱方用机枪打死了140多名犯人,把汽油浇 在尸体上焚烧。有几个人在火海和混乱中逃生。几天后,在大屠杀地点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填满了尸体的坑,那些尸体的手腕上还戴着美国马萨诸塞州 Springfield生产的手铐。
这个填满尸体的坑,还有两处监狱,都在中美合作所的总部辖区。中美合作所是在1943年二战期间根据一项由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委员长签署的协议成立的。(直到我去了美国才知道,协议上宣称的目的是打击两国的“共同敌人”,也就是日本。)

图:白公馆监狱
关押的犯人中大多数是重庆的地下党员。逃生的人里面有一个叫罗广斌的是我父母的熟人。大屠杀十二年之后的1961年,罗和一位合作者出版了一本非常轰动的小说《红岩》,歌颂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英勇斗争。小说里面的角色大多都是根据真实人物写的。事实上,他们先发表了一本短一些的纪实作品《在烈火中永生》,然后才把这本书改写并扩充成一本小说。

图:渣滓洞监狱
随后,一股红岩热在很长时间里席卷了新中国。在六七十年代,这本小说在对学校里面的孩子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反美教育上比任何一本课本都成功。这是我在二年级时读到的人生第一本小说。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和我同样年纪的人,一直到比我们小十岁的,都读过这本书,有些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很喜欢。小说里面有很多生动的严刑拷打场面,那些打手身后常有代表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高参的影子晃动。有这样高昂的英雄主义主题和紧张的地下斗争情节,我得承认这些故事对于年轻的头脑来说的确很有吸引力。我那时候很投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些语言多么鼓吹和煽情。
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话剧,在观众中赚取了大量的眼泪。以红岩为封面的日记本成了重庆最流行的东西。从1963年直到1970年初,我妈和我姐用的所有日记本都用红岩作封面 - 一块红色的石头上迎风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你可以在亚马逊找到这本书的封面。有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有英文版的红岩,但我从没读过。)
在我童年时,小说里面一位英雄在拒绝打手们的逼供时念的诗深深地打动过我。我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首诗也出现在早些出版的纪实的那本书里。书里面说写这首诗的是烈士陈然。二十年后,在八十年代,事实被揭露出来,原来这是小说作者“根据烈士的想法”写的。陈然确有其人,但这首诗不是他写的。 尽管如此,据一位生活在重庆的历史学者何蜀指出,直到2002年,这首诗在课本里面和诗集中仍出现在“烈士陈然” 的名下。
这部小说在毛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化中有着重要位置。书里描写的浪漫化了的英雄主义对于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年轻人有极大和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在1967到1968年发生的仅在重庆就死了几千人的红卫兵派系武斗中,那些在战场英勇冲杀的青年男女会把自己看作象《红岩》里那样的英雄人物,为了他们的崇高理想视死如归,我一点都不会惊讶。 好在我那个时候还年幼;否则我恐怕也会是那些武斗者们中间的一个。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我们都只有事后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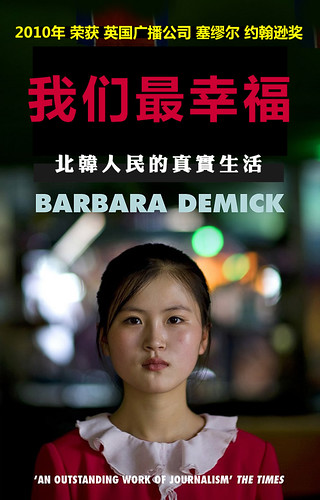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