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中国的媒体、权力与抗议:从文革到互联网时代
原载:《哈佛亚太评论》2008年春季刊第9卷第2期
作者:杨国斌、Craig Calhoun
作者介绍:杨国斌,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亚洲及中东文化系的副教授、著有《中国的互联网力量:网路公民行动;Craig Calhoun,纽约大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学院的教授、美国社会科学家理事会主席,著有《既无神也无皇帝:中国的学生以及为民主而进行的奋斗》、《美国的社会学史》
译者:harry young
校订:杨国斌、@Freeman7777
2004年12月,数名公安人员造访了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目的是为了调查几个出现在其网上论坛的帖子。该组织的管理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几个贴子的存在。毕竟,每天都有许多贴子发布在其网络论坛上,只要是通过了快速在线注册程序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在上面发帖。一般来说,论坛上的讨论并不会触及 敏感的政治性议题。然而,不知何故,几个与法轮功相关的贴子却冒了出来。公安机关发现了这些贴子。经过调查,公安人员发现该组织与这些贴子无任何关系,尽管如此,公安人员还是 要求管理者更加严密的监控其网上论坛,防止类似的贴子再次出现1。
在中国,媒体、权力和抗议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一事件揭示了此种情况的新发展。第一处新发展是使用互联网作为抗议和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似乎,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就冒出了这么几个贴子。很明显,这些贴子带有政府试图压制的信息。第二处新发展则是该事件牵涉到了非政府组织,相对而言,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国家运作的。第三处则是权力运作的模式,以上提到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数以万计同类组织中的一个,其网上论坛则是数百万个同类网站中的一个。然而,即使这样他们仍无法逃脱监视——来自国家权力的监视和压力,纵然在这个案例中政府是进行了适度的处理。
本文将描绘出这些发展的主要特征。为了便于描绘,我们将拿今日中国的社会行动和其历史上的两场重要运动进行比较: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学生运动。我们将集中在三个方面:抗争的剧码(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组织形式和媒体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一些地方的比较相对简略,因此或许该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来对所牵涉到的问题以一种更具历史敏感性的方式去理解。我们的基本论点是:伴随着新信息技术的扩散,大众抗争的形式和政治控制的机制都有了扩展。除 了传统的地点型抗议,新型的网络行动也已浮出水面。尽管国家权力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厉行压制,但是权力运做的模式日趋接近福柯式意义上的“规训”,越来越强调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这些改 变既反映出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又反映出了互联网时代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所发生的更为具体的碰撞。
抗争剧码
集体抗争剧码指的是集体行动的文化方式。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三个阶段,抗争的剧码有所扩展。在每个时期,媒体技术都是抗争剧码变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红卫兵运动时期抗争的主要剧码包括了街头游行示威、贴大字报、印刷和散发媒体材料、公开辩论、绝食、占据公共场所和群众批斗会。当然,这里面的许多斗争形式 都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劳工斗争、五四运动和共产革命3。其中的一些抗争活动,诸如街头游行示威,需要依靠实际的空间场所和面对面的沟通。其他一些活动,诸如印刷传单,需要依靠起码的大众传媒。印刷机、滚筒油印机、扬声器和便携式麦克风是60年代最常用的传媒技术设备。
1989年的学生运动没有再使用群众批斗会这种形式。但是89年运动的其他方面方式却和红卫兵运动时期是相似的。街头游行示威、绝食、大字报和进行公共演讲仍然是抗争剧码中最重要的项目。在60年代,占据公共场所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仅局限于校园或办公大楼,而到1989年, 这种活动取得了更强有力的效果:学生持续性的占据中国象征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另外,一个新项在抗争剧码里脱颖而出——要求与官方进行对话。1989年 对学生抗议者们来说最光荣的时刻之一就是全国电视转播了学生领袖和李鹏总理之间的对话4。
在这两个时期,抗争剧码的主要方式都与实际空间地点相联。大字报沿着行人经常经过的人行道以及集会现场张贴。游行示威在街头或者校园进行。绝食和公共演讲是在公共场所,而不是私人场合进行。抗议就是要进行一场公开表演。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地点赋予了这些表演特殊的含义。因此,北京几乎总是行动的中心而天安门又是北京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然而,国家权力机关和示威者同样也意识到了标志性中心的动员力量。政 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控制 空间的新措施。比如天安门广场现在就被栅栏围了起来。这种变化是打着引导交通的旗号施行的,但对潜在的群众活动来讲是较不容易在广场 上开展了。同样,北京 大学三角地的公告栏已于近日移除,为的是“美化”校园环境,而以前这里是全国性的抗议中心。
1989年 诸如滚筒油印机、便携式麦克风和手持式扩音器等旧式媒体技术设 备的作用仍然突出—虽然扩音器已升级为电子扩音器。然而,许多新的电子技术设备也开始使用,包括电脑、盒式磁带、激光唱机、照相机、复印机、传真机当然还有电视。(60年代,中国只有极少数人拥有电视)这些新型技术设备是中运动剧码不可或缺的部分。比如,商用复印机就成为大规模复印诸如传单之类运动材料的设备。
1989年那个时候最力的新型传媒工具就是电视。电视所传输的一些图像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但是当泪流满面的母亲们恳请政府领导人照看好绝食抗议者时,电视这种新媒介转化了这些图像的影响力。学生领袖们很清楚电视的威力,于是他们要求政府直接直播与李鹏的会议。中国历史上还从没有过学生和一位国家领导并肩相坐于电视之中,进行一场直接对话和火药味十足的谈判。由于媒体文化正处于向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电视将这些情节变成了全球范围的媒体大事件。
如今,人民的抗议仍沿着过去的许多方式进行。农村地区经常是游行示威和占据 公共空间。城市通常是工人罢工。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以网络为形式的抗议和行动已然出现。这种网络行动采用了一种数字化的抗争剧码,从破坏性的直接行动的方式 如黑网站,到非攻击性的行动非破坏性的直接行动的方式如散播请愿 信呼吁信。虽然两种方式都广泛使用,但非攻击性形式更常用些。发帖和转帖这类中国虚拟世界的寻常社交方式有时会转变成极端的抗议活 动,即网络事件7。
非攻击性的数字化抗议采用讨论的方式,发贴,阅读,回应是典型举动。互联网上的发贴是一种虚拟的大字报。从形式、功能和创作过程上来说,发贴类似于大字报。和大字报一样,网上的帖子一般是个人创作、贴在公共空间、表达个人观点。和大字报一样,网上的帖子包括多种体裁(genre),比如散文、诗和 标语。因此,群众抗议的传 统手法在数字时代仍然影响着实践行动。
网上行动的另一特点是其整合了其他的媒体形式和多种抗议模式。有些时候,网络行动就是街头抗议的一种投射。近年来,无数的街头抗议波及到网络,引发了网上的争论和抗议。另一方面在其他时候,网络抗议导致了街头游行示威。因此网络行动融合但没有取代传统的抗议方式。网上活动 人士转帖或者评论报纸上 的文章。网络活动人士可以通过实现向大众媒体或国际媒体的跨界而变得很有影响力。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广西南丹锡矿爆炸案中网上行动的案例。事故发生于 2001年7月17日,导致81名矿工死亡。当地政府和煤矿管理部门掩盖真相长达两周之久。7月27日左右,事故发生的消息首先在互联网的BBS上出现,引发了抗议9。人民日报驻广西分社的记者于7月30日到达南丹调查 该事件,其后,迅速给在北京的总社拍发了一份紧急报告。7月31日,人民日版网上版发布了一条名为“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的最新短新闻。这一报道被众多网站转载。据报道,其网上论坛“强国论坛”上有关矿难的贴子迅速迅增。8月2日,朱镕基总理阅读到人民网的这条新闻,随即做出指示,彻查该案。
组织的形式
文革后,公民组织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无数合法的社 会组织和各式各样的新型组织形式纷纷涌现。虽然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但是媒体技术设备也是这些转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红卫兵组织和派系林立。那时,运动组织的社会基础至少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阶级出身。中学尤其如此,学生派别以阶级出身划线。第二种的社会基础是职业属性。因此,就有工人组织、记者组织、残疾人造反组织等等。在工人组织里,又有纺织工人、钢铁工人组织等等。第三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社 会组织是中国现存的组织结构,主要是工作单位和学校。学校和工作单位正是红卫兵小组首先建立起来的地方。
工作单位中的重要动员手段是贴大字报。在工作单位大院或校园的中心地带张贴 大字报,会吸引成群的围观者并为讨论和辩论 提供素材。对建立组织和招收成员来说,这是很有效的手段。比如,成立于清华附属中学的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以其成员在第一张大字报上所署名称“红卫兵”为其组织的身份认同 。除了大字报,红卫兵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红卫兵刊物。有影响的组织经常出版“小报”。这些“小报”成为组织认同的载体并为宣传和辩论 的有效工具。
如文革里那样,职业属性和工作单位为1989年的运动组织提供了社会基础。学生和市民都是以学校和工作单位来组织他们自己并在各自大学、政府部门、媒体机构等等的旗帜下进行示威。大字报和传 单依然是重要的组织工具。
然而,不同于文革的是1989年的学生运动组织并没有出版任何运动杂志或是报纸,尽管那时有更多的资源存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报纸是派系斗争和组织认同的重要工具。尽管学生领袖和运动组织之间有着内部冲突,但是在89学运中,派系斗争不是问题,也没有很多运动组织。这部分解释了为何运动不存在组织刊物。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运动的展开,学生视占据天安门广场为其中心任务。要保持公众的吸引力就仰赖于吸引中国和世界媒体的注意力。为了这个目的,天安门广场的公众表现比编辑报纸和写文章更重要1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989 年的学生运动在理论上和熟思显得比较薄弱,部分原因是媒体露面的诱惑。
90年代以来组织形式的主要变化,是合法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组织形式的多元化。这些都是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包括有官方注册过的社会组织、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非正式社会网络、学生协会、基于网络的群组和网络社区。
这些变化根植于新的结构条件中。一方面,中央的权力下放和机构转型为这些独立的社会群组空出了些许有限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都市景观也改变了将人们组织到一起的具体空间。越来越多 的人住在远离工作单位的地方,与同龄人疏离了。一些学生开始住到校外,租住自己的居住空间而不是如60年代和80年代一样住在学生宿舍。包括因特网和手机之类的新媒体工具,在碎片化的都市景观中,作为一种组织分散个人的方式变得尤其重要。
中国的公民社团热情地拥抱互联网。他们越来越频繁的使用互联网来组织诸如运 动和申诉 这样的行动。一份对129个都市草根组织的调查显示106个组织(82%)使用 互联网,而69个(65%)在2003年10月拥有网站。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志愿性协会利用网络的水平大致相当。在各式类型的公民 社团中,那些以社会变迁为目的的组织尤其重视互联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旨在改变社会的公民社团“网”已在中国出现13。与较早时期的最著名的社会运动组织相比,他们依赖非对抗性的方法来推动渐进式的社会变迁。
对于一些新型的组织,新媒体技术装备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工具。对他们的生存而言,这些工具也是必要的,这些新型组织形式是 诸如网络社区、网络群组、邮件发送名单和电子邮件以及手机中的个人联系列表等此类 的数字网络。他们成为了现代中国结社革命的一部分14。
网络社区如同邻里社区,不是社会运动组织,也不是倡导网络。但是,只要有合适机会,网络社区会迅速地转变为活动人士的关系网。一般来说,虚拟 网络 通常是建设立 在共同兴趣上的社会关系网。因此, 就有了运动、电影、抚养、武侠小说、时事、环保主义诸如此类的网络社区。各类形式的社会关系网一直都是存在的,并一直为运动动员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这在1960年代和1989年都是真实存在的情况 。然而,与以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为基础的常规社会网络相比,网络社区更间接、更有策划性、更远距离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薄弱了, 但范围要广得多,因此,特别适合于低成本和快速的动员、联盟和动员 。这就是2005年反日抗议里所发生的事情,根据一篇纽约时报对该事件的报道,在那个时候电子邮件、短信和BBS公告栏“激起了公共舆论的愤怒并起到了组织工具的作用15。这故事的一个有趣部分 将直接和下面我们要探讨的媒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关,那就是公安机关 也适应了技术变革。根据上面所引用的报道,在上海计划进行示威游行的前一天,当地警方给手机用户发群发信息,劝告其保持克制。
数字网络和社会行动是相辅相成的。在绝大部分的行动案例中,都是在先前存 在的关系网络基础上才动员起来的。在1989年学生抗议的情况里,当学生按照特定的校园、班级和一群人动员起来时,大学网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某些例子中,抗议导致产生新的关系网。阻止怒江水坝的环保运动就一个恰当的例子。2003年环保运动展开之后,活动人士开设了一个邮件列表来讨论策略和分享信息。在讨论中,有人建议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中国河流”网络来协调和制度化社会活动人士,以便保护中国的水资源。不久之后就开办了一个名为“中国河流”的网站。之后,活动人士开始定期发送电子简报(一个星期除了周末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进行发送),简报主要是搜集关于环境问题 的媒体报道。打印起来约有20页。新闻简报发送到一个大型的个人网络之中。因此,传播简报自身就能起到缝合一个 社会网络的作用。
伴随着数字化网络的出现,个体行为者变得极度重要 。西方社会的网络行动研究发现个体的运动企业家们在以网络为导向的行动中变得十分有影响力17。这与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阐述的理论视界是一致的,现代社会中对政治的再发现部分依赖于“亚政治”("subpolitics")的兴起。他认为由政治系统和社团系统之外的集体或个人来从事的政治,属于亚政治18。中国的网络行动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前面所提到的网络抗议正是由互联网个人用户发起。互联网关系网的逻辑就是一旦信息进入网络,它就可能引发极端反应。虽然不是经 常化为现实,但是不满 总是会潜藏其中。数字化 网络的部分威力就在于其蕴藏了这种政治力量。
媒体技术和转变中的国家权力模式
现代国家既控制信息流动,也控制暴力的使用19。信息控制部分来讲就是对媒体的控制。如此一来,对于某些国家权力机关来说,防止和镇压社会运动就需要控制媒体。从运动发起者的角度来说,挑战国家政权就涉及到为信息渠道而战。
文革时期对媒体的控制集中体现在报纸和大字报上。由于国家的支持,红卫兵组织在发行 其自己的报纸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官方所发布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公告里公开请求“群众”畅所欲言。但是有发行报纸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 言论自由。绝大部分的 红卫兵报纸只是紧跟高层的政治风向。当异议观点出现时,一般来说,他们必须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义的言辞来伪装自己,然而即使如此,鲜有异议者能逃脱镇压的命运。
1989年 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国家并没有支持任何运动媒体。在运动的开始 阶段,国家严厉监控官方媒体渠道。然而,几个条件合在一起削弱了这种控制。1989年,中国老百姓可以从国外多个渠道获取信息。这 些渠道包括散居在外的中国人和在华的外国人士,而那个时候在华的外国人士已经 开始使用互联网。国际媒体详细报道了整场运动。精英内部的分化创造出了更多的开放空间。到最后,记者本身也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结果是,在运动中的一个短暂时期,包括报纸和电视在内的官方媒体变得相当地开放。他们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对天安门和全国其 他地方的运动动员有着间接的贡献。
然而,1989年的媒体只在国家当局在对是否镇压运动犹豫不决时开放过一段时间。一旦开启镇压机器,大众媒体迅速变回了其官方面孔。媒体封锁远比其开放要快得多。国家权力8 凌驾于报纸和电视就在于对机构和手段的的控制——对印刷出版、编辑和记者的控制。这些东西都很容易被控制,因为,他 们是高度中央集权的。
在 网络时代,这种压制型的权力模式仍然在限制着抗争的可能性。中国的网络 活动人士一次又一次地 面临着骚扰,甚至是国家安全部门的逮捕之类危险。然而,正如我们对网上行动所做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网络抗争并没有因为严格的控制就被削弱,相反,却在频率和影响上与日俱增。这些现象都表明中央集权化的权力运作模式已经变得越来 越难运作,因为信息来源已经是去中心化和趋于移动性。手机、电子邮件、网站和其他新式的媒体技术已被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来。在网上普通人自己就可以成为网上内容的制造者。这也意味着尽管事后秩序得到了重建或运动被镇压了,但当局越来越难抹掉行动所留下的媒体足迹。
为了回应这种新的行动模式,国家权力也在演变。在权力的存在模式方面变得更为细致了,在权力的运作模式方面则变得更为有规训了(与镇压时的表现刚好相反)。这从政策和实践两方 面就可以看出来得到反映。在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于2004年9月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以加强“执政能力”,该决议既强调了治理的原则 又强调了治理的手段20。在实践方面,互联网成为了新的权力模式最刻意施加自己影响力的领域。在应对新的社会和技术挑战上,互联网成为中国国家权力试验其自身转型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新的权力运作模式,让我们审视一下中国对互联网控制的 主要特征。首先要强调的事情是,在过去十年间,中国整个网络控制的机制得以强化,新的部门、法规和规章和措施构成了这个体系21。以历史趋势来讲,进行互联网控制的类 型、范围、以及复杂度都 在增加。比如BBS站点现在已经被重点监控,但在早期却不在主要的监控 范围之内。其次,对互联网施动者的控制呈现出等级状态,对某些议题重点监控,而放松其他议题。比如,中国的网民都知道凡是有关89学 运动和法轮功的话题是 完全禁止讨论的,而其他许多话题绝大部分时间允许讨论。
要强调的第三点是,控制互联网的技术包括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被动的控制技术沿着三条主线一直都在演变。一是继续使用镇压手段。包括逮捕网 络异议者或责令BBS版主删除贴。 另一项则是技术控制,通过对软硬件和程序的操控,过滤敏感词并屏蔽属于这个名单之列的网站。第三个就是精神控制。当网民广泛了解了前 两种控制手段,就会发 挥出一种圆形监狱的效果,使网民习惯于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这样被审查者就可以自动检查自己所发的内容了。
为了弥补被动控制手段的不足,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控制手段,以引导网民心甘情愿的和国家所设定的议程(state agendas)保持一致。这些都是治理术方面的措施。例如,为了引导网民跟随官方信息和政策,所有的主要报纸都上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官方的“占领”舆论新阵地。很显然,为了和五花八门的商业门户网站竞争,甚至诸如网上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等最高级别的网上新部门,都不惜以衣着暴露的时尚女模特来装点自己的头条新闻,以 吸引大众的眼球。这些网站通常支持大型网络社区,有着活跃的网上论坛。这些网上论坛与绝大部分的非政府论坛很像,但是,所不同的是他们试图靠发出已预定好 的话题来引导讨论,就如纸版人民日报用来宣传党的政策和引导公众舆论公共舆论导向。
混合使用被动和主动控制技术,会对网络的自由和开放使用产生强有力却又无形的制约作用。在未来的数年间,围绕互联网上的斗争将会始终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主题。
结论
新媒体技术将怎样塑造中国政治的景观?我们分析认为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发展,新的抗争剧码和组织形式将浮出水面已经浮出水面了。从文革到1989年,再到现在,一个清晰而又明了的大趋势就是社会运动从大规模的、集中的、以地点为特征但 很大程度上自发的转向了个人的、分散的和合法组织的社会行动形式。新的形式没有取代常规的抗议和组织形式,但是却扩大了抗 议和抵制的范围。用葛兰西的术语 说,这就是延伸的“阵地战”部分,当活动人士试图扩大被官方所接受且被非官方视为稀松平常事情的边界时,用葛兰西的说法来讲,这些做 法就成了延伸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的部分22。这种情况将如何影响到未来的直接对峙并不不明朗。由于抗议的出路比以前要广 泛很多且只是偶尔有效但却很少转化为实际 的抗议,难道“运动战”("war of maneuver")将无限期延后发生吗?或者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自己是公民而不是臣民,随之加入到抗议示威中来?
相对应于抗议形式和组织的变化,国家权力自身也经历了变化。权力在形式上已经变得更加细致,而在运作中则更讲究规训。
相关阅读: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深度分析”、“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互联网与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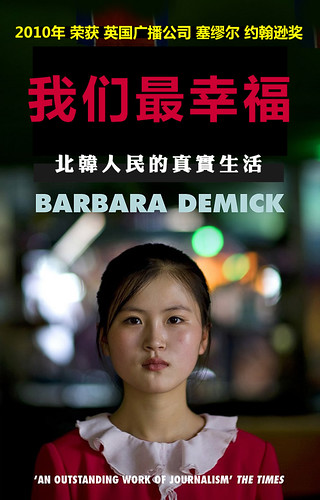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1 comments:
the mixed use of both passive and a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with free network and the
open use of the powerful but invisible restraining effect has lead to struggles as the Internet has always been a subject of political struggle. visit http://www.unn.edu.ng/ for more info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