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09年7月(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专刊)
作者:李静君(Ching Kwan Lee)、伊莱•弗里德曼(Eli Firedman)
译者:推特ID:hsinwang1982
校对:推特ID:Freeman7777
作者简介:李静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著有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2007);伊莱•弗里德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在1989年之后的20年中,中国的工人行动(worker activism)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鉴于工人参与了天安门的大规模骚乱,尽管这一群体在那场骚乱中曾从属于学生,但此后的劳工行动几乎都被限定在了劳工阶层范围内。尽管受到不公待遇的工人群体有所扩大(从国有部门的工人扩大至农民工),尽管劳工行动的形式和事件都在成倍增加,但仍然没有任何动员的迹象表明劳工行动会跨越阶层和地区。
第二,我们注意到,从生产的角度看,尽管在工作场所外获得了更多的(至少是字面上的)权力,工人权力长期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这些权力在过去制度化地体现在技能等级(skill hierarchies)、职代会、民主管理、终身或长期就业以及其他服务性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条款中。新劳动法赋予了工人更多的权利,也扩大了通过行政和司法来解决劳动纠纷的途径。尽管工人在官方限定范围之外掀起并强化着动员,但上述司法和行政程序的确起到了使劳工行动原子化以及去政治化的作用。
曾经使工人能够参与学生反抗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也不复存在了。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打击了具有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信心,自此,他们抛弃了群众运动可以成为政治变迁工具的理念。作为应付支撑天安门反抗运动的合法性危机与社会不满的手段,政府朝经济自由化的决定性转变重组了不同阶层的利益格局。1990年代,即便当共产主义党国体制的官员还依靠其官职和关系受益良多的时候,市场改革使更多的中国人从中受益,其中有教育背景的人和企业家占据了大多数。
中国工人阶层的内部变动也日益明显,在经济变迁的推动下,这一群体的不同组成部份已开始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例如,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和私营经济的扩张,中国出现了一个目前已达1.3亿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10%的庞大农民工群体。1990年代中期,许多国有企业的“重组”(可理解为私有化或破产)开启了一个长达10年的高失业率期。此间,国有和集体企业清退了450万名城市工人。与此同时,世界上广为流行的临时雇佣在汽车制造业这样的支柱产业中也迅速流行起来。现在,自谋职业、兼职、短工、临时工已占到城市就业人口的40%,而且工人阶层的整体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十分有限,即使如此,由拖欠工资、扣留养老金、工厂倒闭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引发的愤怒仍使得劳工骚乱在持续上升,尽管这种骚乱多发生在地方层面。
工人阶层内部仍有城乡之分,在工作收入之外,不同的户籍地位使工人获得了除工资待遇以外的维持生计方面的不同规定,进而在工人阶层内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工人和非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手段也是不同的,这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最后,国家对任何带有跨企业意味的劳工行动都不惜严厉镇压,进一步抑制了基础广泛的工人运动的兴起。
单位侵权与法律赋权
对于中国工人在工作中遭受到的任人宰割的命运而言,官方工会角色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中华全国总工会(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也受到了1989年上半年动荡的冲击。在那一时期,关于扩大工会的自主权的内部争论日趋白热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官员还与学生领袖会面并表达了对独立工会的支持。【1】同其他方面的全国事态一样,6月4日的屠杀终结了工会进一步自主化的讨论。从那以后,没有工会领导人敢公开质疑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这意味着,除了捍卫工人的权利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目标已不可动摇地成了工会首要任务。结果,在基层严重缺乏真正工人代表的情况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由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外在约束的范围内捍卫工人的利益。
作为直接生产者,中国工人极端无权力的处境也可以从严重的拖欠工资事件中反映出来。国务院发布的一项权威统计显示,2006年,按时领取工资的工人不到一半(48%),52%的工人会经常面对工资拖欠问题。【2】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甚至在2004年成为中国总理温家宝个人活动的目的,这凸显了中国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来保护工人。中国的劳工标准已经下跌到了新的深度,从臭名昭著的低工资正演变为因拖欠工资导致的工人生存危机。
如果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管制看似有所松动(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日益资本主义化),它还通过一系列赋予工人新权利的立法活动来推动赋权过程(empowerment process)。这些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National Labor Law)(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the Labor Contract Law)(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the Labor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Law)(2007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赋予工人行使合同权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处的弱势地位。工人只能在事情发生后得到救济,这还要受到反复无常的劳动局和法院有(无)效率以及政治意志的摆布。
因此,劳动立法的增加看似是为了针对不断增长的劳动违法行为以及涉及劳动侵权、劳动诉讼的劳动纠纷,但这并没有为工作条件带来任何改进。权利意识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体制所能满足或容纳的工人要求的范畴。工人较以前有了更多书面上的权利,对此他们也有充分意识。但在现实中,他们在单位没有影响力,法院和政府对其利益的保护充其量也是不稳定的。让人毫不感到惊讶的是,从工人的抗议活动来看,他们并不会随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
过去30年中国式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一个历史条件在于一种具有不断增长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特质的全球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增加。这带来了一个投资洪流,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巨大的市场,为中国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也为通过压榨劳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无异于涸泽而渔。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正在将剥夺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工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推向前台,进而考验中国式发展的极限。如果不均匀的分散式积累使得工人骚乱分布的太过分散、尤其是不至于威胁到整个体制的话,那么由近期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规模的、共时性的工厂倒闭可能会催生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劳工行动。
早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一些中国基层工会被发现它们正在被其成员的悲惨状况所征服被迫去制定组织和行动的新模式来。现在,有迹象表明,企业层面的工会主席正在积极地——即使仍是高度合法地——捍卫其成员的利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昌和深圳的沃尔玛超市通过集体性的议价策略向管理层施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级官员都表达了希望工会寻求集体议价的希望。这一想法是为了减轻更加激进形式行动的压力。但沃尔玛的例子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都表明工会高层只在一定程度上是草根行动的支持者。因此,那些逼迫资方太严厉的企业层面的工会领导人则会冒着被视为“不和谐”的风险,且得不到国家支持。
简而言之,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告别压制劳工的发展策略,为全国工人带来一个能提供权益、法治以及基本劳工保护措施的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手段。理性化集体议价机制的强化和扩展,甚至提供合法的示威游行,都是担心稳定问题的政府需要考虑的。但政府为此必须抛弃以下观念: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立法或管理的方式来消除,可能会使得新劳工阶层作为一种远比今天组织化程度更强的政治势力的方式出现(对多数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理性化的抗争会为中国的一个形式更稳定、更持久的资本主义提供基础。
1. Jude Howell, “Trade Unionism in China: Sinking or Swimming?”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9 (March 2003): 102–22. Available at www.ihlo.org/LRC/ACFTU/trade_unionism_in_china.pdf.
2. State Council Research Office Team, Research Report on China’s Migrant Workers (Beijing: Zhongguo Yanshi Publishing, 2006), 116.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Unported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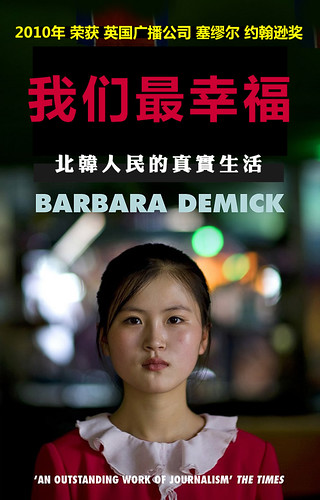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