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ch by Lorne W. Craner
2006年4月10日
傅尔曼大学理查德·莱利中心(Richard Riley Center at Furman University)
演讲人简介:
洛恩·惠特尼·克拉纳(Lorne Whitney Craner),在科林·鲍威尔任国务卿期间担任了三年(2001-2004)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之后于2004年再度成为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主席。在他作为助理国务卿所取得的成就之中,克拉纳先生使布什政府注重中亚人权的政策变得清晰起来并且开始实施第一个去促进中国民主的美国政府项目。克拉纳先生获得了国务院的最高荣誉,他于2004年的时候获得了杰出服务奖(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克拉纳先生所加入的国际共和研究所,该研究所在美国以外开展项目去促进民主,自由市场以及法治,在1993的时候作为负责项目的副主席。他从1995起直到他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一直都担任该研究所主席的职务。在他加入国际共和研究所之前,克拉纳先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亚洲事务主任一职(1989-1992),曾当过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外交政策顾问(1986-1989)。克拉纳先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的成员,并且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美国和平研究所主席顾问委员会(Chairman's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以及一个非赢利支持全世界开放媒体的组织——Internews Network的董事会成员。
克拉纳先生获得了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国家安全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从瑞德学院(Reed College)获得了艺术专业的学士学位。
今晚要求在此向你们发表演讲,我真的是深感荣耀,我是一个终身的共和党人,但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无关党派的,在这项事业中我与我们的民主党朋友们在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里紧密合作。我尊重理查德·莱利(Richard Riley)作为州长和教育部长所做出的服务。《基督教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说许多美国视莱利先生为“本世纪在教育领域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David Broder,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称其为“公共生活中最令人满意的、最受人尊敬的人士”,他所做的事情在政治事务中不是小的功绩。莱利研究所(Riley Institute)继承了他的遗产并且做了大量从推动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到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之间的任何事情。教育对于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想要增强民主来讲都是起码之物,不管是在蒙古或墨西哥还是在马里或是在美国。所以谢谢莱利研究所的各位同仁所做的一切。
我看了今天的活动安排,我在今晚的演讲将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不再是政府官员了,我并不愿强迫你们留下来听我讲话。然而,作为一个还在大学时就一直在研究中国的人士,我确实想把你们的注意力从晚餐上拉到我的讲话上面,我将会谈谈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的状况。我于1981年时首次探访中国,那是自行车仍是标准交通工具的时代,在那时根本就看不到摩天大楼,那是满眼所见仍然全是毛式服装的时代。近十二年以来除了最近这三年(2001—2004年期间调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我一直都在领导着国际共和研究所,我们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在这段时期。
当国际共和研究所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发展项目的时候,为了在中国工作,我拜访了许多不同的专家谈论这种计划对于像国际共和研究所这样的组织来说是否可行,我们还询问了在全球范围是什么做法推动了人权、法治以及民主。那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之后的一段时期,对于以一种透明的、集体合作的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去推动民主的计划有着压倒性的质疑之声。然而,在与那些曾经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人士商量了之后,激励了我们换一种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在一系列讨论上向国际共和研究所倾吐心声,他们感到他们那种以革命的方式去推行政治改革的努力已经遭遇到了挫折,也许值得去思考其他的方式。他们则会继续在中国以外提出进行政治改革的倡议,但他们鼓励国际共和研究所到中国内部去支持系统性的改革并且敦促我们去观察草根选举以及司法改革,以之作为推进更大的自由化、透明度以及问责性的路径。
我们在中国所做的最早期的项目是划时代的。你在当时可以数出许多国际组织——美国的或外国的,在中国的法律以及改革这些议题上工作。许多我们的人权同伴以及民主团体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内部工作的想法是一种疯狂的念头。接下来你所遇见的问题就是,你无法在一个公开或甚至是私人场合提及“人权”这一术语。中国内外没有人谈及建立“法治”(“rule of law”),并且即便是“法制”(“rule by law”)这一术语都还没有进入到中国的政治语言中去。我们支持了民政部致力于发展选举指南并且在民主选举的原则这一事务上训练了数千村级、镇级的官员。我们与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Finance and Economic Committe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合作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在立法起草过程中增强其能力并且打破了国务院对于法律起草的垄断。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执行新法律上我们扩大范围培训了法官以及律师并且向遭受冤屈的人士提供司法救助。
这些着眼于法律以及草根民主的联合项目现在是相当的令人熟悉了,并且现在确实有许多其他组织正在做着各种相类似的工作,包括我们在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的表兄弟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欧盟、联合国发展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以及大量其他的国家级援助机构以及发展部门。自从国际共和研究所深入中国内部工作以来中国的形势也已经大为改变了,“法治”、“人权”这样的术语这些时日以来被用在了中国政府用在了修辞方面即便法律的执行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并没有在实效上有本质变化。中国的政治版图(political landscape)既在更为细微的方面也在更为显著的方面发生了变动,我将在稍后讨论那方面的内容。
然而首先,我想要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回忆我会在十年前做出的对中国可能会发生变化的预言。如果在1996年的时候有人问我,“你认为国际共和研究所在未来的十年里会在中国做些什么”,我很可能会这样回答他:
第一,我会认为我们会在村级选举到镇级选举的工作中取得进步。直到1990年代末期的时候,扩大选举范围至镇一级的压力一直都在增加。1998年的时候,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行了首次直选产生乡长的试验。选举本身被宣布为是非法的,但是结果被允许成立,范围更广的乡镇选举改革可能被允许的期望升高了。当然,实情并非如此,扩大到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在步云试验之后就停了下来。关于扩大直接选举到镇一级的讨论作为“建设一个新农村”的部分政策而重新引起了关注。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中国扩大直接选举的现实已经在现在证明了没有达到1990年代中期所预想的那种效果。
如果我在1996年被问到我们会在2006年的时候做些什么的话,我会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具有监督性质的全国人大。然而,立法层面的改革也没按照1990年代中期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当乔石在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务期间,曾大胆的发出了要求“法治”的呼吁,全国人大在1995年以及1996年的一系列投票中(在那些投票中对政府议案的同意率并没有以前那么高)谨慎的迈出了第一步以履行其法定的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这导致有多篇文章高调的去谈论立法改革,把它作为能促进中国自由化的一条有希望的道路来看待,在1995年的立法会议上,《华盛顿邮报》谈到立法机构正在逐渐的增加独立性,《经济学人》则说它不再是一个它过去一直所扮演的唯命是丛的观众了。在李鹏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全国人大的独立性飞速的在逐步削弱。而各代表团仍然利用一年一度的会议去相互表达对于政府工作以及指示的不快,全国人大并没有作为开放辩论或代议制政府的基石而兴起。
我过去会谈到的第三个领域就是司法改革以及遵守人权这两大块上的事务。例如,我们可能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做出预测,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会废除劳教制度(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或正式批准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但这些目标也没能实现,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时断时续的与中国举行人权对话。但当我成为助理国务卿的时候,我经常感觉中国人肯定一直在认为我没有与克林顿时期的前任谈起过他们曾请求中国做过些什么。(认为这位新上任的助理国务卿不识时务,所提要求与过去相比太过分)
我确实与他们谈过,我知道,至少开始时就知道,我们在与中国进行的人权对话中一直重复于同样的谈话要点清单之中,换句话说就是一直在同样的议题上提出同样的请求。在我上任的第一年里,我有一种沮丧的感觉我们一直都在除了像晋美桑波(Jigme Sangpo)、阿旺桑珠(Ngawang Sangdrol)以及徐文立这些重要政治犯的释放其余没什么好展示的许多议题上转来转去、翻来覆去。正如我的老朋友康原(John Kamm)所说的那样,不照顾好你的人民你就不可能拥有人权,并且我们不能低估这类政治犯的重要程度——自他们被释放以后其他一些人也在过去或会在未来得到释放,譬如热比娅(Rebiya Kadeer)女士。但是也很重要的是把这些人投入监狱的结构改变了,当我在这些方面提出新的议题时,只在老的或新的议题上获得了有限的结果,我们暂时性的中断了对话。
所以如果我们回顾我们可能在十年前所会做出的预言,无论是扩大选举范围,加强立法机构的作用,或废除劳教制度,并且把那样的预言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事实放在一起作对比,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人权以及政治改革的形势并没有改变。然而我确信聚在这间屋子中的专家们会同意我如下的看法,即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动,那就需要我们去更深入的去发掘、去理解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中国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年复一年,我们继续想要通过观察(中国)政府或领导层是否已经(或还没有)采取措施去改善人权以及扩大改革来试着做一个评估报告。年复一年,我们往往发现,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专员(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近期对中国进行的一次访问,间接有征兆显示达赖喇嘛可能会被允许到位于中国境内的佛教圣地去访问,或是宪法修正案的增加条款,承认国家有“尊重和保障”中国公民的人权的义务,然而总的来讲,我们总结认为言论在中国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宗教仍然是无法自由的进行信奉,媒体仍然受到审查,法院仍然不是独立的,犯人的权利没有被完全保护,工人不能自由的结社,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虽然是对中国现状的一个准确的评估,但却不是一个完整的评估,因为它没能观察到中国在对待人权以及自由问题上正在做出的变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当涉及到民主与人权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像我们在过去所期待的那样变动的那么多。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十年里中国人民在意识上的改变很难以量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测度,但是依我之见这样的改变是深刻的改变。在一个相对来讲不长的时期里,数以百计,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数以千计的人们已经涌现出来去推动政府在公民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去接受更大的大众参与,并且遵守法治原则。我们已经在公民社会的扩张上看到了最为戏剧化的改变,我们看到了法律界去推动敏感议题的行动,看到了包括网志作者(webloggers)在内的一些媒体机构以小声但却大胆的声音,想要在民主以及人权议题上挑战当局。
公民社会组织也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长——根据一些统计资料显示,有着153,000个登记注册的组织,并且我们可以认定有好几千这样的组织的是没有登记注册的,这些组织正在做些什么呢?从环境检测到倡导妇女权利,到帮助被剥削的工人讨回工钱以及赔偿金,到在发展以及文化保留等议题上与少数民族团体合作,与那些接受、容忍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人合作。有些团体想要根据法律监督选举的执行并且有团体正在利用策略性的诉讼去提高某些特殊权利这类的议题。甚至有一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团体对中国今年的人权状况提交了一份报告,该团体试图在由中国政府提交的全面颂扬积极面的人权报告以及由美国提交的中国人权报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关注事项,但这份报告无法在当前加入一些如何去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建议。
这些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个体活动人士所做的工作是突破性的、令人振奋的。如果你在10年前问我是否能够有把握认为在中国会出现由中国专家所写的中国人权报告时,我当时很可能会回答你那样的情形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坦率来讲,十年前的中国,在有满屋子专家的氛围里,一说到“人权”这一名词时就迎来了一个尴尬的沉默时刻,之后他们则会快速的尝试去变更主题。这种反差是如何变得有可能发生的呢?这是个很难去回答的问题,但看起来好象是经由中国政府在一些我前面所谈及的同样的结构性议题上所做让步而出现了的小范围的开放空间所导致的,而中国人民则正在把他们自己挤到那样的空间中。给村民有限的,但却是持续的实践民主的能力已经产生出了一种信条即那些权利应该得到尊重。给他们有限的在关于商业的议题上进入法院的机会已经导致了一种期盼产生,即对于仲裁范围更广的争端一个中立的体制应该是可行的。
这些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个体活动人士所做的工作是突破性的、令人振奋的。如果你在10年前问我是否能够有把握认为在中国会出现由中国专家所写的中国人权报告时,我当时很可能会回答你那样的情形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坦率来讲,十年前的中国,在有满屋子专家的氛围里,一说到“人权”这一名词时就迎来了一个尴尬的沉默时刻,之后他们则会快速的尝试去变更主题。这种反差是如何变得有可能发生的呢?这是个很难去回答的问题,但看起来好象是经由中国政府在一些我前面所谈及的同样的结构性议题上所做让步而出现了的小范围的开放空间所导致的,而中国人民则正在把他们自己挤到那样的空间中。给村民有限的,但却是持续的实践民主的能力已经产生出了一种信条即那些权利应该得到尊重。给他们有限的在关于商业的议题上进入法院的机会已经导致了一种期盼产生,即对于仲裁范围更广的争端一个中立的体制应该是可行的。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承认了表明上的国家有“尊重和保障”中国公民人权的义务,这也已经对中国有才华的、勇敢的活动人士开启了去推动国家去实现其承诺的大门。换句话来说,有限的政府让步正导致公民期待以及行动。
这是事实,最为明显的现象体现在了司法改革的领域里。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看到是个体,而不是政府在推动变动。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陈光诚的案子,他是一位盲人,是一位自学成才、掌握法律知识的维权活动人士,他以村民的名义起诉了一个案子,在这个案子中村民感到政府在执行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让他们遭受到了错误的对待,陈光诚现在被软禁在家中,他的妻子也已经被囚禁起来了。然而,他努力让政府遵守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举动是一股更大的驱动中国司法改革力量中的一股。
简单来说,法律界越来越多的在同一时间以一个个案的方式去推动法治。就在上个月,无论是在广东省太石村败选的候选人还是爱滋病活动人士胡佳都宣布他们会对地方当局进行起诉,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赔偿。在太石村的案子中,败选的候选人冯秋盛已经聚集了一批律师想要对选举胜选人追究其选举舞弊的责任。另一方面,胡佳正在对北京市公安局进行起诉,因为他被非法囚禁了41天。这些案子很可能到不了法院,但事实上,这些个体想要通过司法系统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且与10年前的情势作对比的话,会有律师会使这样的案子成立起来。
新闻界已经加入到了推动变动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以及法律践行者的行列中来了。政府和党对媒体实施了非常严密的控制。然而,每时每刻,我们都瞥见中国的第四权(fourth estate)对其充当了党的喉舌这一角色深感不安。中国政府在今年一月关闭了《冰点周刊》,它是中国青年报的每周出版一次的副刊,这在中国新闻界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新闻界的许多人士发出了勇敢的声音,公开批评中国所实行的新闻审查制度。冰点栏目的编辑在他们被调职之后发表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中说道:“人民需要什么?是新闻自由,是由宪法所授予给他们的言论自由;让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其间的大环境的信息是有价值的,调查和暴露不公,支持社会上易受伤害的团体反对那些强势团体,并且要确保人民能生存下去的话需要各种深刻的反省。”
围绕冰点事件的战火目前已经平息,过去一直有(将来也会有)更多的新闻界推动中国言论自由的界限以及宣传官员对其进行打击的事例出现。但是我再一次要说明的是,在10年前的话是难以预测到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来自大陆媒体机构的力量去争取自由的事例的。
我上面所描述到的是来自公民社会、法律界以及媒体的一小部分活动人士的情况。尽管在数量上还很少,但这些个体所发生的呐喊之声得到了中国国内很多人士的认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进程。
就像我开始这次谈话时所提到的那样,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许多人怀疑类似于国际共和研究所这样的组织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是否有意义。中国政府这些年以来在民主与人权议题上的记录已经在一些边缘地带上得到了改善,但总体来讲的话与十年前相比改善得很少,这涉及到了该国政府保护人权以及促进自由的意愿。明显与十年前不同的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以及法治的渴望程度的不断增长。这就是驱动公民社会、律师行动、记者以及网志作者坦率直言增长的原因所在了。
我最后要提的重点是,自1989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去回应国际上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我们已经在联合国以及多边机构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抬高对那些问题的关注,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但光有这些举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办法与承诺改革的人士合作并且我认为那样的人士就是中国人民自身。
我很自豪自己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里担任了助理国务卿一职。我与国务卿以及国会一起合作开启了美国政府第一项得自美国参议院支持的项目,那个项目在继续的扩大。如果我们只看中国政府在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表现,我们很可能会失望。如果我们找到方法去支持一般公民以他们的努力去对抗不公以及使体制按照它自己的法律与原则去运作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成功。
我很自豪自己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里担任了助理国务卿一职。我与国务卿以及国会一起合作开启了美国政府第一项得自美国参议院支持的项目,那个项目在继续的扩大。如果我们只看中国政府在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表现,我们很可能会失望。如果我们找到方法去支持一般公民以他们的努力去对抗不公以及使体制按照它自己的法律与原则去运作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成功。
现在我经常被问及我是如何看待美国是否可能“输出民主”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我们无法做到;我们的民主是一种罕见版本的民主,与我们母国英国的民主不同。而英国的民主与仅与它们隔着一个海峡的法国的民主体制又有所不同。假如我们试着去输出我们的民主,没有人会去接受它;那种民主只对我们美国适用。但是我的确相信有一种普世的、对于自由,对于免于压制的自由的饥渴存在。一次又一次的显示,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促进自由的时候的所作所为会有所差别,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也有这样的饥渴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与欧盟以及其他各地的拥有着不同形式的民主国家一起紧密协调去帮助中国的那些想要看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加入到自1975年以来几十个变得更为民主的国家的行列中去的人士。
今天我站在这里,根本无法预知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自由化的道路。但是当我回顾十年多以来在这些议题上所进行的工作时,我可以说那样的变动正在发生。在变动的方式上处于一个演变的状态,我们不可能在过去预见到,我们也无法预见到它的未来。然而在变动的方式上处于一个演变的状态却也在人权、法治、自由中国的未来方面给了我希望。
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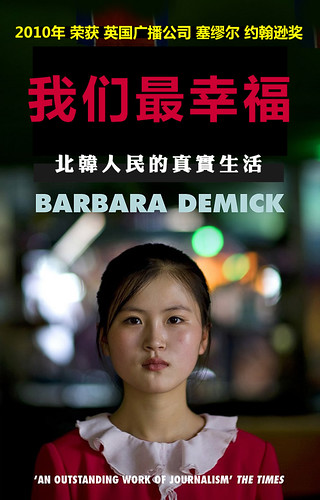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