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恩•克拉纳(Lorne Craner,2001-2004年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在担任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
Lorne Craner:我实际上要更为乐观一些,即便我的发言听起来有点悲观。我不认为将要花费35年的时间中国才会在政治领域上出现大的变动。不过我确实想要谢谢你们给了我与你们一道同台发言的机会。这是巨大的荣耀。我想你们中的某些人已经知道我在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上有着很长期的关注。25年以前当我还有很多头发的时候,我在台湾住了一个夏天。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就进入到了南中国,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20世纪90年代在我第一次担任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的时候,我在这个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我后来到国务院服务的时候,当然也在这个同样的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我确实想谈论一些以民主与人权为议题的事务,它们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是如何被处理的,并且接着会谈论我所认为的我们在接下去数年中在这些议题上所会遭遇到的情形。
当我2001年中期到国务院履职时,美国过去十年中在对华政策上很明显的一个作为是,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衡量中国的人权是否改善有着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看从监狱中释放出了多少异议人士。那种情形的确是真的,衡量中国人权状况是否改善的标准就是由底特律市西北航空公司的747飞机(经美国政府施压,获释以后的中国异议人士都会遭中国政府流放)载出了多少中国异议人士来决定的。
我会告诉你我在国务院期间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在我的办公室与阿旺群培
(Ngawang Choephel)、徐文立等人会见的时候,知道了美国已经确切的影响到了那些勇敢人士的生活。正如我的老朋友康原John Cameron)说的那样,你无法在没有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获得人权。
然而我还认识到当我们把那些(比较有知名度、影响力的)政治异议人士弄出监狱的时候,仍然至少有6000名以上的政治犯在中国的监狱中受着煎熬,那还是我们都知道名字的政治犯。你们一些人已经听到我说起过的那个比率——我被告知2002年是我们迄今在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异议人士上做得最为成功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让10名异议人士获得了释放。但还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仍有6000多名的异议人士被关在监狱里,假如没有人再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关进监狱的话,以2002年我们获得异议人士的速度来计算的话,需要600年才能把那6000人弄出监狱。那比裴敏欣所提到的(CCP的寿命还剩)35年要长久很多。
所以当我们继续致力于在诸如热比娅•卡德尔(Rebiya Kadeer),我们采纳了布什总统推动民主的理念——布什信条(Bush Doctrine),这是在布什总统这一任期以来一直被称作的名称——并且把它在中国付诸了实施。我确实认为在911以后,在中东地区我们在民主以及人权上做出了政策转变。这些政策转变体现在了在中国推动民主与人权的手段中,当却得到了比他们原本应获得的更为低的注意,但我认为它们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为了在中国推动民主,为了确保异议人士能够有一天留在中国并且让他们可以成为记者或政治家,为了帮助这样的进程早日到来,我们就开始制定了一个中期以及长期的战略。
中期战略是围绕利用始于《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的、已经诞生六十多年的人权的全球标准。我们开始与诸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on Human Rights)这样的多边机构以及诸如酷刑报告员(rapporteur on torture)的各种报告员机制,并且强烈倡议他们在人权事务上中国接触。
这些机制在中国有潜力导致人权状况不仅在个体的政治异议人士身上得到改变还能在整体人群中得到改变。这些机制的存在显示了人权不只是,就像经常被引用的那样,是一个美国才关注的问题,而在事实上是所有国家都要遵循的一个全球标准。既然如此,则我们坚信,要使得联合国做出的批评所针对的对象更难去忽略个别国家,使得这样的批评为被批评国更为容易的去接受。
第三方面,亦即我们所制定的长期努力,是要围绕着中国国内的各类行动,那些行动是由类似于国际共和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样作为的团体所做出的,通过农村的选举,城市地区的司法改革,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使诸如中国人大(NPC)和省级立法机构这样的既存建制变得更具代表性来帮助改善中国在政治上的民主。正如Ying Ma前面说道的那样,当我在2001年进入政府的时候(用于这些事务的开支)大约有200万美圆,主要是来自高宝玲(Louisa Coan Greve)所在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大约有200万美圆在私营部门中进行这样的工作。在2002年,我们第一次开始为在中国进行的这些工作募集款项,开始时募集到了400万美圆。到我2004年离开政府为止,我们募款到的金额已经上升到了1600万美圆并且我认为在明年将会达到2000万美圆。
就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任务而言,我们知道如果能够与其他国家密切关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我们的努力成果是可以被扩大的,尤其是,试图找出一个在这些议题上的共同议程来。从2001年开始,通过所谓的伯恩程序(Bern Process) 来进行协调,使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所有国家得以聚集起来进行信息交流并团结到比一般想象的程度高出很多的更大的团结程度上。再次要讲的是,如果美国是要推动中国的变动,如果伦敦当局、哥本哈根当局、奥斯陆当局、阿姆斯特丹当局、堪培拉当局也要求中国作出变动的话,那么这种变动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加剧。
我的确同意能够记录下来的达到了明显成功效果的这些措施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地看一下我定义为中、长期的那些战略的效果,毫无疑问的是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动并且我认为会最终证明(这些战略)是有其成果的。
短期之内的战略是希望中国政府释放政治异议人士,除了少数重要(获释案例)以外, 譬如:热比娅•卡德尔(Rebiya Kadeer)和王有才,我们过去几年中并没有看到许多政治异议人士被释放的消息。这样说,当然是意味着没有2002年释放的那么多。虽然如此,我知道我在国务院的继任者巴里•勒文克朗(Barry Lowenkron)随着我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 Jr.)一道,继续致力于具体案件的解决。话虽如此,我们不能完全用释放异议人士这一个衡量标准来确定我们的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否,我认为那将是一个忽视了(解决问题的)途径(avenue)的错误。
首先,无论它们位于这个世界的什么位置,那些致力于让任何国家变得更民主的人士理应去知道,那就是当狱警正在殴打他们(被关在监狱中的异议人士),并告诉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正被关在监狱里或谁也不会去关心他们——信奉民主的人士理应知道有些人、有些地方正在想办法把他们弄出监狱。此外,我相信中国的第一位民主化的总统是目前生活在中国的人士,基于过去在其他国家的经验,那位领袖很可能是今日仍被关在监狱里的异议人士。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这方面的努力。
在中期战略所关注的议题上,许多联合国的调查员自2003年以来已经为中国政府所承认。最近、最引人瞩目的访问是联合国酷刑问题调查员(UN Rapporteur on Torture)完成的一次(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调查并且发布了一份非常诚实的报告。问题现在是,如何去对待这样的报告。例如前任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范博文(Theo van Boven)对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的人权状况做过一次相当坦率的评估,但报告中所发现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引起乌兹别克斯坦当局的重视,他们根本就没有针对那些问题做出一些纠正的行为来。然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意味着它不想要参与到文明化的世界(civilized world.)中去。为了使其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不可能做出那样一种决定来。因为中国寻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事务参与者从而得到他国的认可,让美国、欧洲以及联合国三方联合给中国领导层施压让他们结束那些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报告中发现的弊端,这样的机会是存在的。
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第三个方面是致力于推动与扩大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这一长期战略的层面。记住这些结构性改革是中国人发明的产物,而不是西方进口之物是重要的。他们通常所追求的结构性改革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确定的说,他们的确是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些改革的结果没人会期待在中国产生革命性的变动,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看见这一场景的发生。
但是我认为这些努力在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真正的、有意义的变动。让我提三点征兆给大家听吧!
第一,毋庸置疑的是在许多这样的事务上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善——那些事务都是民主化发展的基石。最为显著的就是公民社会这个例子。在不久之前的2001 年,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真正的非政府组织(NGO)。而在今天,大约有100,000个登记在册的非政府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实际正在运作的该类组织数量比这个登记在册的数字还要来得高。
非正式的取消了国家对社会生活很多领域的介入已经为公民参与活动(citizen participation.)创造出了新的机遇。中国人民正在寻找方式以组织他们自己的机构去回应社会需要,去表达怜悯与关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政策制定的程序。这个事务本身就是一项非常显著的发展并且这是一个在过去一些年里根本无法看到的事情。它所显示的作用是给予了中国公民——像地球其他公民一样的公民以机会,带着做出变动的愿望,将涉入到公民生活(civic life)中去。
我们也在乡村选举中看到了有限的实质性的改善,大部分这样的选举尽管是非法的,实验性质的乡村选举,无论你怎么称呼他们。尽管政府举办这些选举的目标是想控制腐败,保证社会秩序,而不是想要去发动民主化,这些年来许多地区的乡村选举已经发展成了真正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村民已经在诸如竞选(campaigning)以及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这些选举手段上获得了经验,并已证实让他们充分参与到民主程序(democratic process)中去,他们是能胜任的。
在一些农村公民认为他们没有受到地方领导人公正对待的情形中,他们毫不犹豫的把他们选下了台。尽管中国政府继续声称农村地区没有为实行民主做好准备,因为大量农村人口没有接受过教育。在这种选举开展后的十七年时间里,农民事实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民主意识(democratic consciousness)。确实,当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时,会有这样一种情形出现,即中国农民是最理解民主的一些基本信条的人士。
与过去十年相比较,在城市地区有了更多司法救济的途径。中国律师的数量以及在民事法庭提出诉讼的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城市居民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系统去保护他们的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权利,如果不与政治相关的话,甚至会起诉政府。简而言之,他们正在发展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意识(rights-based consciousness)。这一切表明法律行动的效率已经上升并且对司法系统的信心也越来越高。
第二个征兆是这些结构性变动正在产生的结果听起来是吊诡的(paradoxical)并且甚至可能听起来是残酷的,但它与农村、城市所兴起的我刚才所描述过的对于责任制、民主以及个体权利的期待是相关的。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压制性的社会里,当更多压制手段被用来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有变动发生。
对于这些改善的效果最好的证据是中国政府的反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改革在某一个领域里进行得太快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尝试着想要跨越省际界线形成了一个组织网络或律师们挑战中央权威或一家报纸在他的报道中涉入了太多他被禁止涉入的内容时——改善现状的动作就通常会被暴力的手段给阻碍住。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各类组织(包括公司、行业、社团等)不断增长的压制。不仅是压制个体异议人士还是对结构性改革的压制,譬如:关闭非政府组织,关闭报纸并开除他们的编辑人员,殴打曝光选举舞弊的非暴力活动人士或监禁为异议人士辩护的律师。始于2003年,北京当局清楚的决定,认为始于90年代初期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进行的太过快速了。他们害怕你们(其他发言人)一直都在谈论到的再次发生混乱的情形,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变形成了一种短视的、对稳定和秩序近乎痴迷的偏执状态并且对于任何他们认为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事情表现出越来越低的容忍。
结构性改革效果的问题以及第三个征兆,中国公民已经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尝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就像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他们也很喜欢自由。他们如此的喜欢它以至于想要的更多并且他们正在做着争取那些目标的努力,即使北京当局试图压制这样努力。十年前,甚至三年前,人们从没听说,乡村居民联合到一起来抗议中国的威权统治者(authoritarians)。但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村民们注意到了反应灵敏,经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与未经选举的、威权主义的村镇、省级和全国政府的差别。中国政府也许是擅长于群体控制的政府,但它却无法阻止这类示威事件的急剧性扩张。
任何去过中国农村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十年前的村民(作者在发言中使用到的是”citizens”一词,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我会选择不同语境,以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来翻译这个字眼)甚至从未思量过选举一个全国性政府的可能性,现在则会问为什么那样的举动是不被允许发生的。因为他们很难阅读到(能报道出新闻真相的)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这种情况即使到今天仍是如此,相比较选举造假事件或没有代表授权的征税或腐败、胡乱开发这些事件的报道,人们更可能阅读不到的是关于一个村子中发生的暴乱事件的报道,
相似的情形发生于90年代中期,城市的居民被告知要开始用司法系统去纠正违法行为,于是他们信以为真了。他们已经推动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且他们已经开始在法庭上辩护那些被指控为政治罪行的案件,即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要面对来自官方的骚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会向政府发问,为什么贫穷的乡村地区的农村居民们获得了直接的民主选举,而他们这些城市里的居民却仍被认为素质没有高到可以实行直接选举呢。
其实,我觉得北京当局在这一点上面临两种选择。可以尝试以及阻碍诸如这样的变动并且继续要面对创记录的农民暴动,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有74,000起。或他们可以扩大改革去
设法满足人民要求更多自由的需求。到目前为止所显现的证据是他们将会试图去阻碍这些改革。十月份所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再次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公民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民是不同的,他们的能力较差,教育程度比马里或蒙古这两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还要来得低,马里或蒙古可是公认的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哦,这说明了你不必拥有一个中产阶级就可以推动民主。
只有通过扩展自由——例如,通过把司法改革从城市地区扩展到农村地区,对农民开始实施真正的、先前对他们不公的司法救济并且通过在城市地区复制已在乡村地区实施的政治改革,因此之故,城市居民就拥有了真正的政治自由以及真正的政治代表——只有通过扩展这些自由才能使中国拥有避免我们最近已经看到的各式各样动乱的希望。
话虽如此,我认为布什政府已经到位的提出了一项好的政策——短期之内致力于异议人士的释放,在中期的时候通过多边机制,而在长期的时候则是推动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结构性变动——我并不意味着做出这样的暗示,即除此之外更多的事情就无法去做了。让我给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
第一,任何政府总是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当我还在政府服务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当我离开政府部门,担任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的今天仍然是这种情况。首先,我认为,总统可以在对这个问题上做得更好。他在2002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期间发表了一次杰出的演讲,他公开得高调指出了他对于在中国改善人权的个人兴趣。就像我们在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所看到的那样,没有任何替代物能替代总统对于自由的言论,因为外国领导人必须要加以回应。
总统在最近一次访问中国的表现无法与更早前的那次访问相媲美。我有幸在2002年时旁听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议并且据我所知在他多数近期的访问中,他也同样强烈的在私人会见时提到了如上的那些观点。但我觉得他被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所误导了,(那些中国通)认为他在北京的时候不应该公开地强调人权或民主。这对总统(想要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计划)来说是不利的。
第二个方面需要更高度去关注的是在人权和民主事务上与盟国进行协调。我先前提到了
伯恩程序(Bern Process)。在我们于2001年开始这个程序之前,我们的议程确实与他们之前做的在共同点上是更多的。如果这个观念,而不是细枝末节而只是这个观念在副部长级或国务卿自己出面的层面上被推动的话。这个程序可能被执行得更为严格并且在与北京打交道的时候要来得更为有效。
如果我们更加紧密地与盟国加以协调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奥运会即将来临的时候施加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压力。可以施压给各种改革,以确保北京当局在对赛事进行报道的记者群到来之前看起来达到最好的水平。
我也知道有很多在中国运作的公司想要在劳工标准以及支持公民社会发展上做出更多努力。我离开国务院的时候,我所在的人权以及劳工事务局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着手展开并且这些努力应该得到支持。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直在寻找好政府的供应面(supply side),诸如村民选举、法治、法院工作、立法机构等等,审查在这些方面中国是否可能接受美国援助。我们还应该寻找需求面,就是要找到那些要求拥有更好政府的公民们。
我要把大战略(grand strategy)留给我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老同事们。我乐见于看到当局承诺进行的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起一个更为紧密的关系。我也同样乐见于看到总统成为首位访问蒙古的美国元首。美国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受到欢迎部分原因在于北京在处理与一些邻国的关系上已经过早的表现出来好战的势头,尤其是与日本。
我所遇到的来自该地区的人士正在把他们的忧虑转移至对一个更强有力的威权主义中国的本质的担忧上。在这处背景里,我会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昨天日本的外交部长甚至公开呼吁中国加强政治公开度。我还希望大家注意一篇文章,我想它是发布在今天的华盛顿邮报上的,是关于亚洲首脑会议的,这意味着中国要把美国排除在该会议之外,而事实上,正是他们自己正在被其他国家排除在该会议之外。
这使我想到了最后一点要说的事情。中国做出反应的一个要素是他一直在尝试的,我已经提到过的、由布什当局所激励的更多、更大的政治开放,以及压制由政治改革所引发的高度期望。
第二个要素是与2003年左右所突出的外交政策相关。中国越来越发现最与其相似的国家都是地球上最具压制性的政权。中国总是可以交到像伊朗和苏丹这样的朋友,但我们正越来越看到中国为那些较不具有深远重要性的,诸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卡里莫夫(President Karimov of Uzbekistan)或缅甸的梭温(Burma’s Soe Win)或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Zimbabwe’s Robert Mugabe.)这样的外国领导人铺设红地毯、与他们把酒言欢。
正如其试图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售卖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中国今日正试图出口“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那就是:你可以在没有政治变迁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发展。可以忽略对卡里莫夫总统或穆加贝总统的注意,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并且最后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有什么充分理由去乌兹别克斯坦或者缅甸 或者津巴布韦进行投资。
我们应该没有担心过,就像你今天提到的这个问题,中国模式会压倒“自由在全球范围内的稳定发展”(“global march of freedom”)。北京当局为取得持久性朋友所做的这些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像穆加贝这样的独裁者将不会持久。美国在冷战的三分之二的时间中,从与独裁者共舞的经历中学习到了,在这些国家产生变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当民主来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人民会记得是谁在帮助、支持他们的目标、事业,是谁站在统治者一边。北京当局与卡里莫夫总统、穆加贝总统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姻亲关系,但如果只是为了中国自己的长远战略利益,中国的统治者就应停止推销北京共识,并提出更具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结交更高级别的友邦。那就是我们国家在 20世纪70年代所学到的教训并且布什总统已经在911事件后的中东地区一直所应用的战略,现在轮到中国了。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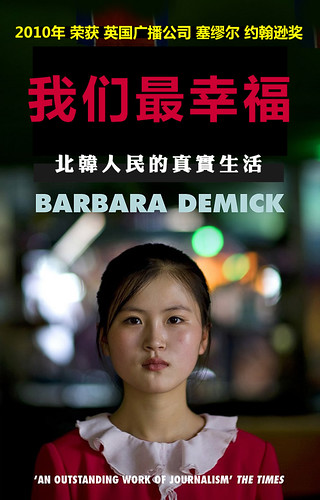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