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Andrew J. Nathan is Class of 1919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coedited The Tiananmen Papers (2001), coau- thored China’s New Rulers (2002), and coedited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2008).
2009年《Journal of Democracy》7月刊(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专刊)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关于这类的政权是如何保持住权力的以及它们是如何改变的这方面的疑问过去一直都在吸引着那些极权主义,法团主义、军事统治、官僚制威权主义以及比较共产主义的研究者。但是这类研究主题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随着民主的历史性胜利似乎是不再时兴了。确定的是,中国的政权仍然握有实权,但它似乎又是正在进行自由化的;较小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不常见的;并且君主制以及神权统治似乎正在枯萎当中。
但是历史保留了它的狡黠,不是黑格尔式的透过盲目的人类行动来达成历史目的论的方式,而是后现代式的以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的逆转来回应了我们的诠释。天安门事件二十年之后,中国的威权主义的韧性仍然使我们吃惊着。在1998年和2003年对中国民主的希望做出探询之后,《民主杂志》决定再次进行总结。2在这期的专题中我们考虑了政权的前景是否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多极化,社会动荡,一个兴起的中产阶级以及互联网上的新自由而已经有所改变了。
如果不是文章篇幅有限,我们还可以问问西方教育以及文化,环境退化,政治腐败以及汉民族民族主义,少数民族民族主义、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其他不间断地测试中国公共秩序总体框架的大型因素的影响:前面几页说明丰富了我们对于作为一个仍然很少被理解的新类型的中国威权主义体系的认识,这是一个国家主义中又有着企业家精神,政治垄断中又有着个人自由,人治化权力运作中又有着司法程序,镇压中又带着回应(responsiveness),政策一致中又带着分权化的弹性,虽然进行信息控制却又已经产生了一个媒体圈。该体制二十年来一直保持强大不是通过扼杀变动,而是通过孕育它来达成的,不是通过保持体制一尘不变反而是通过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结构去满足新需求。今日的体制提升了能干的领导人,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进行政治接班,产生了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并且吸收了大众的支持。也许掌握这些动态将有助于刺激对于比较威权主义体制(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 systems)进行分析的研究复活。
未来的阴影
但是和所有当代的非民主体制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的体制也拥有一种与生俱来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事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经由一致同意(common consent)产生的政府要更为具有合法性。尽管该政权宣称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是建立在它为人民服务以及统治是合乎人民利益这些事情之上的,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公民今天还是接受这样的宣称,3该政权承认,并且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权威从未顺从于大众的意见并且它也从来没有意图想要那样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政体被打上了权宜之计的烙印,是一种临时性的和过渡性的需要以满足时间上的紧迫性。而民主制度,相反,常常引起失望和沮丧,但他们没有面对比他们有更好声誉的任何其他政体形式。5威权主义政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并不是永远会持续下去的。就他们的多样性以及长久性来讲,他们都生活在未来的阴影底下,对于存在的挑战是易受伤害的,而这是成熟的民主体制并不要去面对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戏剧性的,具有明确准绳的朝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这是到目前为止保持了一个低姿态以求避免镇压的中国律师、上访者、博客作者和记者,以及更广泛圈子中的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宗教团体所组成的维权运动的希望。他们希望,这一政权将变得陷入到为维护其统治它已经创造出来的诸如法院和新闻媒体这样的安全阀式机构的逻辑里。(真这么操作的话)党接着就会发现它自身被迫要去与一个平等的强势的民间社会共存,中国将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需要一个迎接变革的戏剧性时刻。可以称它是一种新类型的转型,不是奔溃(旧体制完全解体)、解脱(extrication,,转型发生时既有政体的规则被废止,但是威权统治者仍有机会参与协商下台的谈判条件),或(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或公开或私下达成的)协议(pact),而是平顺转型(segue,意思是转型前后的体制有延续性,不需要剧烈变动)。
中共在顽抗那样的景象到来。它的领导人从天安门事件中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拒绝与社会的平等对话。正如支持镇压的前总理李鹏在他与支持对话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危机期间所辩论的那样,去允许示威学生去“与党和政府平等的进行谈判”将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否定整个社会主义体制”。6随后在东欧和苏联所发生事件确认了中共领导层的看法。7这个政权愿意去以任何方式进行改变只要有助于它掌握权力,但是它不愿意去放松对于自主的政治势力的禁止。政权改变,如果它来的话,它更可能是通过某种程度的破裂发生才导致的。但是中国的转型将不会和苏联的转型相似。中国并没有处在一个它无法承受的军备竞赛之中。它也没有与美国进行一个安全领域的过度竞争。它的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它总人口比例的5%-6%,并没有像苏联般超过了半数。它也不是一个加盟共和国式的联邦国家,加盟共和国是有权从中脱离出去的。
中国的转型也不会与台湾的转型类似。8中国政府并没有必要去纳入以前所排除在外的多数族群。它不会去允许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或在竞争性选举中训练人民。这个国家也不像台湾那般如此的依靠美国。
中国未来最有可能的转型方式仍然将是天安门事件那样的模式,有着下面三个要素一起作用才产生的:1)不满现状的公民所构成的强劲的多元性(在1989年是由于通货膨胀和腐败,在未来很可能是因为失业以及环境灾难或某种形式的国家耻辱);2)一次向分散化的各种社会势力发出了信号的催化性事件,告诉他们:改变的时机现在已经到来;3)领导层的分裂(不管是由于性格差异,权力斗争,武装警察以及军队的不确定支持,或意识形态的分野) 使得来自最高层的反应变得不确定或虚弱并且允许挑战迅速增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权才认为自身是脆弱的,这从它所做出的大量去防止以上三个因素冒出来的努力上得到了证实。它力求去保护公众免于受到经济不稳定的影响,在主要的社会群体中收买合法性,控制坏消息,取缔动员,分化以及镇压反对派,监控民间社会,控制互联网和手机之类的联络工具,加强警察和准军事力量,总之,就是去使它自己的内部分化不让公众发现因而使他们认为社会动员的机会结构仍然是没有希望的。截至目前为止,这类努力在对国际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工人的影响方面是成功的。分散的回到了他们所来自的农村地区并且得到了由政府刺激计划所产生的工作,农民工一直没有向政府发动挑战,并且现政权成功的抑制了08宪章的影响力,08宪章拥有最为广泛的支持基础并且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对其统治原则所进行的挑战中在智识层面做得最为精致的一次。
但是潜在危机的要素可以在任何时间结伴而至。如果人们设想中国的体制面临到诸如美国、英国和日本最近所经历到的那些遭遇:不成功的战争,暴跌的经济,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挑剔的媒体,在文化认同上深度分化之类的各式各样问题,很难想象中国的体制会存续下去就好比想象成熟的民主国家会崩溃那样。使这类政府的危机避免成为政权的危机的做法是公开化异议的文化,强健的法治,在回应公众不满时有制度上的能力去更换领导人而不需要去变更整个体制。中国假如在1989年选择了其他的路径,它今天可能已经拥有了这类稳定化的特点。没有这些作为,威权主义的政权将不断上演像是一组杂技演员在走钢丝的戏码,在避免所有危机的同时使它的动作合在一起是毫无瑕疵的。今日,我们的撰稿人证明了,现政权正努力去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它无法承担滑倒的代价。
NOTES
1. Amos Perlmutter,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0).
2. “Will China Democratize?” Journal of Democracy 9 (January 1998): 3–64; and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January 2003): 5–81.
3. 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9–37.
4. See, for example, “Zhonggong zhongyang guanyu jiaqiang dang de zhizheng neng-
li jianshe de jueding” (“Resolution on enhancing the governing capacity of the CCP”),
19 Septemb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26/content_2024232.htm.
5.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Asia’s
Challenged Democracies,” Washington Quarterly 32 (January 2009): 143–57.
6. Zhang Liang, compiler,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118.
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8.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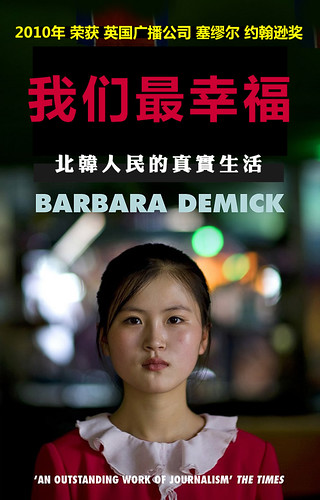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2 comments:
读者来信评论照登:
--------------------------------------------
我以为,很难,三个条件不是不可能,可是,看中国5000年历史就知道,只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不反抗就会死的时候,才会有大多数的响应。
现在的困难,没有到要死人的地步,或者说没有大规模死人的地步,中国的刑罚,法家都是非常有思想地位的,所以,中国历史可谓灾难深重,远比欧洲中世纪更可怕,更让我们更能忍受。
看每个朝代的历史,成败兴衰都是这样的,反抗,反抗,呵,世界上和我们一样诛九族的都么?400年前还多了个第十族-学生。
我想说,共产党看到这点,它明白,只要还能过下去,反抗就会微弱,中国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宗教冲突,也没有那么深的信仰。如果说为什么,中庸吧,为理想而死的确是英雄,我们也崇拜,但大多数时候,是“逼上梁山”。
把劳动力压榨到最大化,但不可以过线,只是这条线,比大多数观察家以为的,小得多。
犬儒主义也毫无疑问助长了这个。
所以,89年后,政府做了什么呢?政府让大家全部信仰金钱了。
鸟翼一但系上了黄金,就不能再飞翔了。
当然,政府也犯了另外一个错,呵呵,统治是需要信仰的,如果大家都只信金钱,毫无疑问,没有人信党了。而牺牲,是维系党的生命力的一部分。没有愿意牺牲的人,党也不党了。
so,现在有开始讲责任,讲奉献,但对我,80后,和更小的孩子而言,我想,迷失吧,也许,只是也许,西方的60年代将在中国这一代手中重演。
没人知道中国会怎样,预言和历史学家都不会有答案,但,不要动荡,中国这个国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
所以,海德公园不也不允许提倡暴力革命么。
摧毁和重建,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
Inspiring story there. What happened after? Thank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