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政策评论:为什么中国成功了而俄罗斯失败了?
来源:胡佛研究所出版的《政策评论》 杂志
作者:保罗·R·格里高利(Paul R Gregory)、周晓(Kate Zhou)
发表时间:2009年12月15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对:@torrentpien、@Freeman7777
两条不同的经济道路
1978年11月的一个黑夜,安徽小岗村的18个中国农民秘密地把村里的土地分给个体家庭耕种,这些家庭将把国家征缴之后的剩余留给自己。这样的分配是非法的,非常危险,但农民们觉得值得去冒险。在这个故事里,时机是最重要的。农民采取行动之后一个月,党的“改革”大会召开。结果,号角不曾吹响,自发的土地已分配蔓延到其他村落,经济改革开始了。一个农民说:“当一户人家的小鸡得了鸡瘟,整个村子都会得。当一个村子得了它,整个县都会被感染。”
两个国家分别进行的改革,结果可以说大相径庭。长期萧条的中国农业开始繁荣兴旺,不仅体现在谷物上,而且体现在所有的作物上。当农民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把他们的收成带到城里,为买食品排的长队开始减少,然后消失。国家副食垄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终结了。在苏维埃俄国,尽管有国家的大量补助,农业却继续停滞不前。超级大国的公民不得不再次忍受食糖定额供给的屈辱。
当农民骑车或坐车把他们的收成带到城里,为买食品排的长队开始减少,然后消失。
这两个例子是对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和邓小平的中国所进行的改革的恰当叙述。我们的叙述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相矛盾。标准的记述是,中国的成功是因为一个英明的党的领导层有意选择渐进主义,在天安门事件后拒绝民主、继续保持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并且在很多年里小心谨慎地引导这个过程。对俄罗斯的叙述是,俄罗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激进的戈尔巴乔夫忽视了中国改革模式,前进得太快,允许党的垄断土崩瓦解。这一标准叙述是不正确的。与流行的说法相反,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同意改革方案,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邓的掌权地位。中国改革派官员鲍彤后来如此承认:“事实上没有讨论改革,改革不在议事日程上,在工作报告中也没有提及。”1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只是简单地回应(明智地没有反对)了主要是发源于农村人口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冲动。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著名描述“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正确的,是中国人民把石头踩在自己的脚下。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成为党的总书记。那时,他已经知道中国改革取得成功。与流行说法相反,他的改革是紧紧模仿中国的。他建议把土地租给农民,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小型合作经营的发展,以及建立合资企业。不同在于,戈尔巴乔夫是从上层推行这些改变,基础是城市经济,其中所有的公民实际上都为国家工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者被忽视了,或者它们在付诸实施时带来了错误的结果。自下而上的改革在中国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俄罗斯遭到了失败。
两个国家都是在一个痛恨改革的领导人(或领导层)消逝之后开始重大的改革。邓小平及其盟友经历了与强硬派短暂的权力斗争以后,在1978年接替了毛。戈尔巴乔夫继承的那些人是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最初受益者,那时他们作为年轻人迅速取代了那些被处决的人。容易被遗忘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是他们中最后一个;当他死去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寻找一个相对较新的人。对于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对于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毛的过度激进——大跃进时的饥荒和文革中的“再教育”——仍记忆犹新并充满个人体验。但斯大林把独立思考的党的官员从形体上消灭,毛则允许他们存活下来,在毛死后取代了他。戈尔巴乔夫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千锤百炼的党员从党的阶梯上爬起来的,尽管表面上被视为一个改革者,戈氏几乎没有改革理念。他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改革事实上没有胃口。邓小平也从未提出过一个改革方案,但他充分明白不去反对有效的改革(“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现实的改革,无论是基于高层的授意还是从底层汹涌而起,都需要一个改革的民意基础。在中国,大量人口从毛时代的浩劫中恢复过来。农村居民尤其明显,他们见证了大跃进的混乱,目睹了父母儿女在1958-1961年的大饥荒中饿死。他们明白需要照顾好他们自己。城市精英在文革中被迫离开城市,在农村工作、生活,接受再教育,整整一代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在俄罗斯,上一次饥荒还是在30年之前。战后,几乎没有人因为政治罪行被处死(政治异见被精神失常所取代);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之后,古拉格(集中营)逐渐被拆除。所有人都活在这样的格言之下:“我们假装工作,你们假装付工资。”2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基本对体制满意,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国有企业或国营农庄的的怀抱中。3中国拥有一个改革的民意基础,俄罗斯没有。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得到有改革头脑的人的支持。他听到的是经济学家的拙劣建议。他受到顽固官僚的反对,但国有企业的经理们支持他,他们迫切地想在构想拙劣的改革中获取利益。
农业
中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农业都通过武力实现了集体化。在俄国,1929-1931年的强迫集体化和反富农化(dekulakization)运动引发农村的内战,内战被残酷地镇压了。较为富有的农民家庭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流放,剩下沮丧的农民被纳入农村政治当局严格控制的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农业必须按照莫斯科的调子跳舞。在中国,1950-1953年,土地被从所有者手中夺走,随后在农村的清洗以200-5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土地改革向农民分配了田地,但无视农民的抵制,没有分配所有权。单是在1950-1951年间,71万2千人被处决,129万人被监禁,还有12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4
尽管看到了俄国集体化的灾难,毛还是从1958年开始强迫他的农民们加入大型合作社。所有的财产,有时包括家具甚至刀叉都成为共有的。在这两个国家中,集体农场必须把农场的产品以指定的低价交给国家。他们必须服从来自莫斯科或者北京的轻率的指示,例如大规模生产玉米,在适合水果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或者停止生产“令人颓废的”茶叶。虽然这两个国家都未间断过对自留地的压制,但自留地使农场的家庭能够维持生存,并且向城市提供部分肉奶制品、水果和蔬菜,农民在街角摆摊兜售这些产品。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都继承了非生产性的集体农业。苏维埃俄国的农场部门深陷衰落之中,以至于这个传统的谷物出口国现在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谷物。到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农场的人口相比从前的规模萎缩了四分之一,只有年老的工人留了下来,在国家农场里敷衍地工作,或者照料他们的自留地。他们早就变成拿工资的工人,享受养老金和社会化的医疗保障,虽然这些保障的质量不怎么样。在中国,农村居民占据人口的80%,和俄罗斯的农场工人相比,他们年轻而有活力。他们没有俄罗斯农场工人那样的社会保障。在中国,只有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私营农业。小型私人土地在中国存在了2000年。景山(Jingshan)村一个老农民简洁地回顾这种历史记忆:“家庭农业就像人对吃的需要、对性的需要、对孙儿们的爱一样自然。我们热爱家庭农业,因为它给我们某种自由。领导们觉得他们知道如何让我们更好地生活。但这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5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农场居民能够回想起1920年代私营农业的最后记忆。
戈尔巴乔夫1988年向农民提供的协议是,他们可以从国家获得自有土地50年期的租约。他的提议是一个“承包体制” ,租赁者将固定份额交给国家,但可以保留剩下的部分。事实上没有人接受他的提议。俄罗斯的农民们深深地固定在国有农业中,在这里他们可以“拿到”种子、肥料和工具,其准则是“它们属于每个人,因此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中国的农民没有得到如此慷慨的条件。相反,他们开始偷偷地分配土地,由每个家庭把定额的收成交给国家。戈尔巴乔夫从上层号召非集体化,中国的农民的非集体化则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承包责任制”,最开始是冒着受到严厉处罚的风险。没有领导们,没有面对面的对抗,它就这么发生了。当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党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挡,而且可以从正在发生的某些事中获取利益。到1982年,超过90%的农村居民都已从事家庭生产。即使邓小平正式支持基层农村改革,他并没有给农民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的长期承诺。农民们在1982年得到的只是1-3年的承包合同,只是到了2003年,国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才允许长期的租约。
企业
自发创造的农业承包体制意味着对农业产品的新的供给,这些产品需要走向市场,而市场仍有待创立。在贸易改革上,再一次,俄罗斯和中国的道路出现分化。
戈尔巴乔夫不满于现状,发动改革以扩展市场和私人贸易。他的改革失败了。呈现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个中国商人创立的未经允许但却已成事实的市场。他所做的一切是在该市场明显成功后将其合法化。随着数百万农民成为卖家,竞争驱使对城市消费者的价格降低到合理水平。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掌权之时,国内贸易由国有的贸易网络掌控
戈尔巴乔夫把俄罗斯的影子经济视为他可以发展的资产。他在1987年5月颁布关于合作经营的法律,该法律的目的是把过去非法的很多行为合法化。新的合作经营可以使用房产、拥有设备,而且可以按市场价销售产品;主要的限制是他们不能使用雇佣劳动力。“新俄罗斯”的第一份财富事实上是合作经营的产品。戈尔巴乔夫希望合作经营能够成为企业家的源泉。随着1987年5月的法令,合作经营形成了右派和左派,其中很多是在国营企业内部,其他的则得到社会组织的支持。合作经营法确实使得影子经济走向公开化。然而,没有预料到的是,合作经营者们几乎没有给消费者增加福利。相反,他们通过钻计划经济的漏洞,把国有部门的利润重新分配,装进自己的口袋。合作经营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以“小型企业”的虚假名义形成的;他们从国有企业以低价收购原料,然后以很高的“合作”价格卖出去。他们通过贿赂贸易官员,运用影响,倒买倒卖稀缺的外国商品。一个典型的合作经营者是前克格勃官员(与作者中一人熟识),他运用自己的关系,从国有贸易公司以低价购买个人电脑,再倒卖给消费者,一切都打着科学院的幌子。他后来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国会代表。与这个前克格勃官员一样,新俄罗斯人从合作社法令孵化出来,向俄罗斯人提供了初次品尝“资本主义”的苦涩,随后俄罗斯人与非法收益紧紧联系到一起(到今天还是如此)。
另一个巨大的对照应当强调:俄罗斯合作经营运动中的“企业家”主要是城市居民。俄罗斯农民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农场改革,他们没有参与。他们不生产需要运输和销售的产品。中国第一批企业家主要来自乡村,他们是依靠把农业产品卖到城市而起步的。
中国的私人贸易从草根阶层发展起来,从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和繁荣,因为它满足了最根本的需求。农村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巨大的农业剩余,必须通过国家体制之外的渠道被销售出去。农业产品必须经过长距离的运送,要么直接运送,要么通过中介——违法的、没有可以通过法院执行的合同。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但一开始是数十个,然后是成百成千的企业主们成功地挑战了合法的界线。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商人-企业主必须为运输和销售农业产品创造出全新的制度。一旦到位,他们可以把这些制度应用于其他的产品和劳务。这些最初的企业主不是国家改革的受益者。相反,他们必须找到摧毁社会主义制度障碍的途径,并且创造出市场。中国的企业主必须处理好收益和安全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一个错误意味着被充公、监禁或者更糟。6企业主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无法获得国家的资本。国有银行在1988年6月以前拒绝向任何私营经济提供服务,甚至还有严格限制。
中国早期的商人-企业主们必须首先克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问题。从1940年代晚期以来,国家把长距离的贸易视为一种投机,一种资本家的行为,把那些参与者视为罪犯。在1960年代末期,这种商人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一些人丢掉了工作,或者被送到劳改营,其他人被列入需严密监控的街道监管名单中。即使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早期,警察追逐农村摊贩、没收物品的景象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7一个中国的企业主把他早年的生意冒险比作一个未受训练的杂技演员走在一条拉紧的绳索上面:“我为巨大的市场机会激动不已,但又害怕重新回到该死的牢房号子。那时我过着一种老是汗流浃背、彻夜失眠、心惊肉跳的生活。”8在整个1980年代上半期,江苏北部的农民在他们的自行车上堆满鸡、鸭和其他家禽,越过扬子江,通过铁路把他们的产品运到扬子盆地的城市中心。“百万雄鸡过大江”是这一景象的描述。9到1983年,重要城市中的消费者大多在自由市场上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不去政府的商店。在一年的时间里(1979-1980年),绝大多数国营蔬菜市场都出局了,只有得到高额补贴的北京和上海的市场除外。
中国绝大多数早期的企业主拥有农业背景,或者至少来自农村家庭。
一个巨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建立仅仅只是开始。一旦一种制度建立起来,其它制度不得不跟上。私人贸易商在没有旅行许可的情况下经营,不能在国营旅馆住宿。因此,企业主们发展了一个私人旅馆网络。关于勤劳的企业主的典型故事是他们提供国有经济无法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一个来自湖南的少数民族妇女开始做生意是在大城市里买进鞋子,然后在她的家乡保靖卖出。她跑一趟需要1-2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只好扔下三个孩子不管。她生活得很节俭,却投资盖新房子。当卖完鞋子从山上返回时,她收购草药、蘑菇和其他地方特产,在县里的市场上把它们卖掉。经过10年的辛勤工作,并帮助她的孩子们获得大学学位后,她才安顿下来,每个月从这些年修建的6座房子中收取租金。她是家乡新富人中的一个。
中国绝大多数早期的企业主拥有农业背景,或者至少来自农村家庭。2007年的中国首富是南部省份广东一个贫穷农民的女儿(译注:指碧桂园的杨惠妍),其家族在1990年代早期获得大量地块和农村的问题资产后变得富有,当时还不存在房地产行业。在1990年代中期,她的父亲开发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买得起的别墅和度假村。10其他农村企业主没有进入前十大富豪名单,但他们成功的故事同样激动人心。1980年代早期从公社中脱离出来之后,农村企业主离开他们的村庄,在大城市建立了餐馆、洗衣店和很多小的生产企业。朋友和亲戚跟着来了,像一个温州企业家所解释的:“我的邻居在上海开了个小的洗衣店,挣了些钱。我和我的兄弟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8万块,加上我们的2万1千块家庭储蓄。1995年我们去上海时,发现那里已经有太多这种店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转而开干洗店的原因。”跟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中国的企业主是通过3F(friends朋友、family家庭、fools傻瓜)开始他们的生意的。
腐败出乎意料地成为企业主的武器之一,没有腐败他们可能无法找到那条区分成功和监牢的狭窄小道。企业主不得不“头戴红帽”(把家族企业注册为正式合法组织的一部分),给创立的企业披上集体企业的外衣,或者找个“大人物”、“岳母”作为保护他们的庇护伞。没有这样的掩盖,他们无法开收据、保留账簿、交纳税收、签署合同或者开银行账户。没有这类设施,很多农村私人企业无法逃过对私人公司的沉重税负。福建一个村的两个农民创建了一个包装厂,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工厂属于那两个村民,但工厂在名义上属于村集体。通过使用集体的名义,私有的村工厂交的税更低,甚至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在向村长付了5千元“管理费”,向镇政府另外付了1千元之后,这个村工厂可以毫无阻碍地做生意了。
中国企业主在私有市场制度建设上的成功可以用一些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说明。在1978年,国有企业生产了中国80%的GDP,农业公社生产了其余的20%。11没有私人企业。到1997年,中国有96.1万个私人企业和2850万个小型家庭私人公司。到2002年,非国有部门占GDP的份额超过2/3,其中真正的私有公司占比超过一半。2004年,300多万家私营公司雇佣了4700多万工人。121980年之前,中国的创业活动是非法的。今天,中国有4000多万企业主,他们的企业雇佣了2亿人,生产2/3的工业产品。国家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农民市场和私人贸易开始萌芽的现实。产品质量的改善和漫长食物线的消失向城市居民以及政府领导人证明了基层创业活动的力量。国家无法做到限制此类活动而不激怒全体人民,尽管它不断在尝试。1988年,政府把拥有私人企业理论上合法化,但实际对私人城市市场上施加严格的限制,包括征收不合理的管理费。
私有企业起源于农业,扩展到城市,然后作为以农村为基地的产业又返回农村。很多大型私有制造公司在农业大省(浙江、山东、广东、湖南、四川)发展起来。中国最大的农业企业新希望集团是刘氏兄弟建立的,他们离开城市,在四川的一个农村地区建立了他们的公司。王国端是来自南部广东省的一个农村企业家,他建立了最大的冰箱制造企业科龙集团。远大,中国最大的空调制造商,总部位于农业省份湖南。中国第一家汽车出口商可能来自“农业腹地省份安徽,奇瑞汽车的所在地。”13温州农村的企业主向城市提供资本和消费品,他们的私人资本被用于为机场和高速公路建设融资。
全球化与外国直接投资(FDI)
让我们转向两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上截然不同的经历。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在同一个起点上开始的。每个国家都拥有一个严格的中央控制体系,实行外贸垄断。毛和斯大林都相信自力更生,不愿意依赖其他国家。苏俄在东欧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共同体,限制了对西方的依赖。两个国家都失去了战后贸易的巨大扩张机会,当时他们转向了国内。
已经有很多文献记载中国在吸引外资、技术以及在国外市场销售制成品上的成功,而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问题上的稳定掌控也是不能否认的。向世界市场开放一个经济体不是底层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并不是没有参照模式。他们不会不注意到邻近的东南亚四小龙引人注目的转变。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可以追溯到1980年,当时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在邻近香港的地方建立起来。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在1978年,中国的贸易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低于1%。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占全球贸易的6%。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超过日本和韩国。
戈尔巴乔夫无疑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印象深刻。俄罗斯经济的全球化在他的改革计划中扮演着中心角色。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的合资企业法(相伴随的还有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是模仿中国之前几年出台的法律,理由充分。到他掌权的时候,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为庞大。戈尔巴乔夫希望开放俄罗斯可以使改革没有阵痛。在他当政的第一年,他预测会有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的生产“加速”,这些新技术主要来自西方合作伙伴。14
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共产主义的过去,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为它培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俄罗斯刚开始的时候状况好些。戈尔巴乔夫把俄罗斯的大门打开,但没有人来,这与中国的经历恰好相反。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但它使得中国的成功更加奇妙。
为什么俄罗斯未能成功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西方投资者不得不对于在俄罗斯投资投以怀疑的目光。只有一小部分俄罗斯人拥有世界市场的经验,而他们全都为外贸垄断机构工作。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外贸行业是怎么回事、一旦出现合同违约会怎么样、在私人财产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投资的安全,或者这些投资如何整合进仍旧是计划的经济中去。西方在意的是,在没有任何关于地下资源的法律情况下,被要求投资于巨大的能源基础设施。问题仅仅是,在俄罗斯对外国投资的渴求和西方资本冒险投资于俄罗斯的意愿之间,没有可信任的中介。
俄罗斯所缺少的,是一个海外的俄罗斯侨民群体。有少数俄罗斯人移居美国和以色列。但中国有一个“大中华”,在香港、台湾、澳门、东南亚和北美有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这些“大中华人”,尤其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在大陆还有根。他们展示出商业上的机敏,而且明白一个低工资的、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国家,在东南亚繁荣中的核心地位。这些大中华人作为媒介,可以向投资者解释如何投资,与谁投资。谁是可以信任的?谁不可信?哪个政府的官员们是可靠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人在商业上是成功的,在中国境外拥有产业和资产——它们可以作为抱怀疑态度的外国投资者的担保品。
海外华人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难民,他们在香港、台湾重新安家,中国上的关于全球变化的第一课是来自邻近的香港。在共产党统治之前,广东省会(毗邻香港)的居民被认为是精明的城市人,而香港则充斥着农村的土包子。到香港腾飞的时候,数百万广东人逃到香港,参与其经济奇迹。广州的亲朋好友们排着长队等着得到他们在香港的朋友和亲戚穿过的衣服。年轻的城市女性只想嫁给有海外家庭关系的男人。15当中国政府首先在深圳(靠近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香港难民的故乡)、厦门(靠近台湾)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中国人直接从香港那里借用新的规则和制度。广东的企业主复制了香港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其他人则和香港的小企业主一起建立了合资工厂。
利用家庭和文化联系,香港表哥们得以克服官僚习气。香港商业大亨胡应湘(普林斯顿毕业生)建立了第一条收费高速公路,连接广州和香港,承诺15年后将其转让给中国政府。香港拥有亚洲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为中国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正是通过香港,中国的货物第一次接触了全球市场。台湾投资者在1990年代早期开始涌入中国,通过香港绕开经营上的限制。他们将中国作为制造基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竞争。到2004年,台湾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接近3%。2001年,中国自己向全球化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WTO成员资格激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贸易伙伴。16
国有企业
在两个国家,国有企业构成了重工业、国防、交通和金融业这些计划经济“制高点”的核心。如果不摧毁计划体制以及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它们不可能转变成私人拥有。国有企业范围内的生产被纳入国家计划中,它们不被允许倒闭。相反,它们是在“软预算”之下运作,其亏损自动被覆盖了。它们归有权势的部长、地方官员和党的领导人管理,雇佣了数百万相对被惯坏了的工人,这些工人依靠国有企业提供工资和福利。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利益群体,反对有意义的改革,或者试图顽固地把改革转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从改革的第一天开始就必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则可以选择推迟解决国有企业问题。
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全体居民事实上为国家工作的经济体
这两个国家,采取的办法都是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保护,给它们更多的决策权力,提供激励以更有效地经营企业。尽管两个改革的组合和背景不同,但它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国有企业仍被要求向计划体系提供计划内产品,但他们可以保留超过计划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按更高的价格销售。经理和雇员们可以保留更多的红利和投资利润。它们可以通过与其他国有企业的“直接联系”,增加投入品的购买和产品销售。在两种情况下,计划者设定计划体系的产品的价格,在国有企业之间交换。因此,同样的产品(例如,钢铁)可以按两个或者更多的价格来购买和销售,最低的是国家的官方价格。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都在无意之间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租金生产机器”。19在两个国家,经理们在他们的工厂内建立了小企业和合作经营,他们可以用来剥夺国有资产。他们将生产从计划转向合作经营部门,在那里他们可以卖更高的价格。通过以国家固定的低价购买投入品(经常是从自己那里买),然后转移到合作生产部门,最后以高价卖出,获利变得轻而易举。
两国应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寻租和腐败的方法都是出台严格的破产法。戈尔巴乔夫1987年的企业法确实要求国有企业消化自己的成本,声称不会有救助。但没有破产发生。不盈利的国有企业争辩说,关闭它们将会令倔强的工人们流失街头,使国家失去基本生产能力。国家救济继续毫无争议地存在。1986年,赵紫阳和邓小平治下的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部破产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把改革思想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党的总书记)赶下台。当国家在1998和1999年再次开始强迫破产时,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己的目的,把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卖给贪婪的前政府官员和政治上联系紧密的私人公司。
企业法的失败在俄罗斯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计划生产土崩瓦解,国有企业相互之间拒绝供应,计划经济实际上停止运作。20中国的强硬派仍有破坏改革的力量,与此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保持着彻底推动改革的权力。他走得如此之远,甚至拆散了党监管经济的机构,引发强硬派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政变。1991年12月,苏联分裂成15个独立的共和国,开始他们自己独立的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继续低效的、腐败化的运作,但它们没有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
中国的国有企业继续低效的、腐败化的运作,但它们没有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像俄罗斯发生的那样。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国有企业继续得到国家救济。尽管国有部门现在占GDP的1/3,但超过70的国有银行贷款流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下降,但继续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森林和水资源。他们是腐败的主要来源。根据一种估计,寻租和官方的暴利约占中国GDP的20-30%。21
中国如何能够振兴如此低效率和腐败的国有企业呢?中国传说一般的增长是结合了高速成长的农业、私人经济、国际公司以及缓慢增长的国有部门的结果。而且,中国的国有企业可能不总是低效率的。在俄罗斯,对于国有企业没有标准。在中国,国有企业与合资企业、外国银行共存,他们面临着不断侵蚀其市场的私人企业的竞争。合资企业提供了衡量国有企业表现的尺度。在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他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的9倍。22
其他经济成分的力量给了中国领导层喘息的空间,去试验不同的方案,比如将国有企业重组为企业集团(戈尔巴乔夫想做但没有成功),设立控股公司,以及在深圳和上海建立股票市场来为重要的国有工厂筹集资本。国有企业的问题也在通过自然损耗而自行解决。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95年的11.8万家减少到2005年的27477家。23自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减少了4400万个,一半以上是在制造业。这种损耗有一部分可以简单地归因于腐败,经理们将国有企业“自发私有化”,把它们的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
对于现在的教训
自下而上的改革不可抵挡,因为它不需要讨价还价,避免冲突,就像一场不可阻挡的瘟疫一样散布开来。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通过除掉改革者的领导人或者通过高层的阻扰而轻易扼杀掉。中国式的改革在特殊的情况下成为可能,这些特殊情况包括小型私人农业和贸易的传统、刚刚经历的浩劫和清洗、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体的落后等。如果中国领导人面对与戈尔巴乔夫同样的环境,他们可能会遭受痛苦的失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面对无法解决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问题;中国则可以选择坐视它们萎缩到相当的规模。每个国家的现在都受到过去的影响。在两个案例中,他们的初始改革都开始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中国后来的领导人没有改变这个进程,每一个新的党的领导人都继续推行前任的政策。在俄罗斯,苏联共产党被解散了。叶利钦统治下民主和市场经济有了爆发式发展,随后这两方面在普京当政时期都出现了倒退。现在,双头统治者主宰着俄罗斯,其中一人拥有克格勃的背景并且重新恢复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
中国和俄罗斯的道路继续在分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着国家控制的“经济制高点”萎缩。中国的企业主已经不顾一切阻力建立了私人制造业。大型国有公司无法与私人的国内企业或外国公司竞争。他们靠国家补助和支持维持生存,但很有可能,有一天这些都不复存在。俄罗斯的企业巨头是苏联企业的直系继承者,没有一个是白手起家从基层建立起来的。在叶利钦治下,它们被私有化给那些城市中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内部人。绝大多数被剥离的资产 ,在后来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向他们承诺财产权利安全之后, 有些开始产生股东价值 。在一个重大的逆转中,普京决定经济制高点属于国家,于是俄罗斯的大公司重又被国有化。那些仍留在私人手中的公司则需了解他们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股东利益服务。
两个国家似乎都从另一个国家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对于中国是:政治改革将会摧毁共产党;对于俄罗斯是: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威权领导人才能使改革成功。中国的执政党继续拒绝政治上的改变。普京和梅德维德夫则继续强化威权控制。
俄罗斯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政治化运作和国家所有的企业无法参与竞争。俄罗斯当前的领导人控制越来越多的工业经济,同时令他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俄罗斯这些新的国有企业面对的竞争很少,甚至没有竞争。俄罗斯的新领导人已经把外资赶了出去,而私人企业主在逐渐占领市场的同时会面临人身的危险。俄罗斯的巨人们——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卢克石油公司(Lukoil)、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等等——很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低效率,为政治目的而不是经济收益而运作。
中国的领导人们面临一个有趣的困境,而解决困境的方案将会影响他们的未来。从2001年开始,共产党着手将企业领导人吸纳入党国的网络中。作为党国的精英成员,中国的企业主通过利用关系而不是靠企业家才能来获得盈利机会。2007年,党和国家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物权法,将私有财产合法化。这一法律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但它是通往创立一个法律规则来代替政治的随意性关键的一步。中国的企业主们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是在一个公平参与的法律规则环境下作为企业家参与竞争,还是利用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来获取“不劳而获”的利润?如果选择后者,他们将会是杀鸡取卵。结果会让中国陷入像俄罗斯那样的停滞不前的寡头统治中。拿破仑曾经说过:“让中国睡吧,因为当她醒来时,世界会为之震动。”一切取决于,醒来的是哪一个中国——一个企业家的中国还是党的寡头官员的中国。
保罗·格里高利是休士顿大学Cullen杰出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周晓是夏威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和比较政治学教授,她是《农民如何改变中国》(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Westview, 1996)、《中国通往自由、基层现代化的长征》(China’s Long March to Freedom, Grassroots Modernization, Transaction, 2009)的作者。
相关阅读:
译者频道—看世界
译者频道—经济风云
译者频道—深度分析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中国经济
译者“Andy Cheng” 的更多译文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看世界”、“译者频道—经济风云”、“译者频道—深度分析”、“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中国经济”、“智库报告(稿源)”、“译者Andy Cheng”索引。
notes
1 1 Bao Tong, “A Pivotal Moment for China,” Radio Free America’s Mandarin Service (December 12, 2008), available at http://newsblaze.com/story/20090106100021zzzz.nb/topstory.html.
2 2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Harper and Row, 1987), 19.
3 3 Michael Ellman and Vladimir Kontorovic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An Insiders’ History (M.E. Sharpe, 1998), xxi–xxiv.
4 4 Xinwen wubao, “The New China’s Oppression Campaign against Counter-reactionaries,” China.com (2006).
5 5 Kate Zhou, interview with Chu Bo, farmer in Tongxi village (February 1986).
6 6 Keming Yang, “Doubl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Summer 2002); 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7 The struggle between urban police and street vendors was common in major cities. On many occasions, on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ly witnessed police chasing and then beating street vendors in the early 1980s in Wuhan and Beijing (1983 to 1984).
8 8 Kate Zhou, interview with Mu in Beijing (July 1997).
9 9 Kate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Westview Press, 1996).
10 10 Robin Kwong, “China’s billionaires begin to add up,”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2, 2007).
11 11 Guojia Tongjiju. Zhongguo tongji nianjian 1987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1988).
12 12 “Private enterprises expanding quickly,” People’s Daily Online (February 04, 2005).
13 13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08).
14 14 Gorbachev, Perestroika, 19.
15 15 Kate Zhou,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Ouyang in Guangzhou, (August 5, 1986).
16 16 Nicolas Lardy, “China Enter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2002), 2.
17 17 Bao Tong, “A Pivotal Moment for China.”
18 18 Deng Xiaoping, “To Speed up Reforms,”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People’s Press, 1988), 1444.
19 19 Anders Aslund, Russia’s Capitalist Revolution: Why Market Reform Succeeded and Democracy Faile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7), 58.
20 20 Paul Gregory, “Bureaucrats, Managers and Perestroika: The First Five Years. Results of Surveys of Soviet Managers and Officials,” in The Soviet Economy Under Gorbachev (nato, 1991), 188–202.
21 21 Wu Jinglian, “shichanghua congnanlai? Daonanqu?” [“Whither the Reform of Market?”] (September 12, 2008).
22 22 John Whalley and Xian Xin, “China’s fdi and Non-fdi Economie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Future High Chinese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s, May 2006); Matt Nesvisky, “Will Super-High Chinese Growth Continue?” NBER Digest (November 14, 2006).
23 23 Wayne M. Morrison, “China’s Economic Condi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to Congress (May 13,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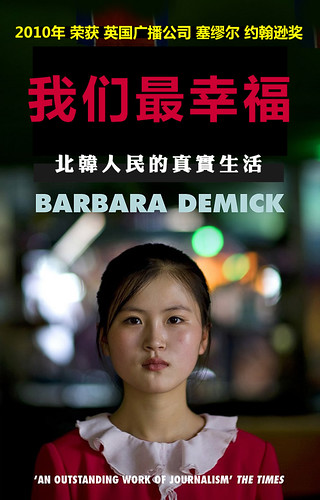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