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现代性的选择压力下(selection pressures of modernity),民主制度将显示出面对新兴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具有优越的调适能力与回应能力;但与此同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也是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2)。
然而对亨廷顿来说,强有力的威权主义统治赋予的比较优势在本质上是短命的及过渡性的;从长远来看,政治权力必须通过制度化才能变得有效能。而在这一方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极大的两难处境:如何创造出更有效能更有回应力的政治体制,同时无须放弃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列宁主义式的垄断。
为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不满与压力不断加剧以及加强共产党政府“执政能力”的需要不断增长所困,中国领导人近几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用来逐步增强社会纳入、协商与吸纳的机制,同时并没有扩大政治问责制、责任制与大众赋权的范围。这些手段主要包括:
·创立省、市与县级“电子政府”网站,用于公开政务并获取公众对政府工作表现的反馈意见;
尽管这类行政调适的首要目标是提高政府的执行力与回应力——或者用现在的行话讲,叫“国家能力”,然而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紧张状态的持续恶化——反映在大规模社会抗议事件的频率与剧烈程度的急速上升上(4)——使人们对这一新的、改进了的“协商式列宁主义”的中国模式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同时,这也重新提出了关于短期政治秩序与长期政治发展间关系的亨式问题(Huntingtonian question)。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化。到19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在讨论一个新的、后列宁主义的中国发展模式。
这种有时被概括为“小国家,大社会”的模式,被预想为党和国家机关的大规模裁撤,并伴随着在草根层面上一个有生气、自发的与自治的结社空间(sphere of associational life)的兴起(5)。这种模式暗示了对众多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与利益集团合法性的承认。
在1980年代晚期,一项旨在促进社会政治更加多元化的运动得到了一部分年轻的中共改革者的赞同,并得到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的支持。在1987年10月第13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赵紫阳摒弃了传统毛泽东主义认为的在社会主义下必须“统一舆论”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应当注重倾听公民们利益与观点的分歧并作出回应。
尽管打算逐步地转型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基于利益的政治过程,但赵紫阳因主张权力分立、多党竞争与政治言论自由的西方式宪政民主缺乏拥护者而止步了。在注意到现代化与经济改革具有内在的混乱性与压力性后,赵紫阳(一如亨廷顿)认为其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构成不稳定性的因素”。因为这个原因,他建议(同样是以亨廷顿的方式)向政治多元主义的转型应当“按有秩序的方式逐步”实现(6)。
中共重新树立起的反对政治多元主义的决心——如有必要会强行镇压——被1991年苏联解体带来的震惊进一步加强了。在此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严厉谴责了戈尔巴乔夫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重申他们对协商式列宁主义的信奉,同时再一次强调了维护“团结与稳定”的决心。
随着政治改革被无限期搁置起来,中共在1990年代对付社会不满的主要策略就是分化瓦解。当问题变大到无法忽视的地步时——比如农民抗议乱收费或非法的土地强占,下岗工人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与养老金,或者愤怒的家长要求对灾难性的学校爆炸及大火事件进行调查——这些事件会基于个人,做特别安排的方式去处理 。只要类似的事件还是局部的,它们就能为决心保持社会表面稳定的家长制作风的政府所解决。
这种将行政性冲突通过局部化特别处理的方式进行遏制的策略,包含了被黎安友称为“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实质,其将经济自由化与紧密的政治控制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在社会不满只是小规模并十分分散、以及当受侵害的群体间进行交流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是十分成功的。然而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随着现代化通讯工具——手机、个人电脑、互联网及SMS文本消息——的普及,弱势群体的不满被动员起来了。由于不满的社会化表现变得数量上更多、规模上更大,它们对政权的潜在政治威胁也变得更大起来。
在1990年代晚期,面对着中国的党和国家与中国社会日益脱节迹象的不断增长,江泽民试图提高共产党正在不断降低的威望。他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邀请中国新兴暴发户阶层里的企业家与商业精英加入共产党。通过将这些新的经济精英们纳入中共的“大篷”中,江泽民希望能扩大共产党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以此提高其回应力。
在厌恶风险的江泽民几年前隐退之后,普遍预料他的继承者胡锦涛可能会放手去实施一项更进步的政治议程。确实,在2004年9月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委员会坦率承认了共产党统治的脆弱性并确认了其合法性危机不断加深的事实,故而出现重大改革的前景看起来也瞬间光明起来了:
“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7)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宣称“党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8)
如果说四中全会小心地开启了进一步政治开放和多元主义的希望,那么不久这种希望就被胡锦涛压制了下去。在2009年9月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明确地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并不意味着放松甚至放弃中共55年来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也是明确载入中国宪法的……。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中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译注:摘自原文)(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在四中全会不久后的一篇冗长批示反映了中共领导层对权力的进一步控制。批示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共要扩大自己主政者的角色。其中,曾庆红特别强调中共要加大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日程和审议活动的控制,加大中共和政府的交叉和融合(以及模糊职能责任界线),以及增强中共对利益集团活动的监督。(10)
中共上述的三个“当务之急”与赵紫阳1987年提出的改革举措针锋相对,这毫不让人奇怪。在这个意义以及其他意义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号召更像是在强化中共传统的治国理政垄断权,而不是一份政治开放和改革的宣言。
寻求一个“和谐社会”
最近,中共强化执政能力的动力看似矛盾地与新儒家哲学的复苏走到了一起,去追求一个“和谐社会”。中国总理温家宝2005年3月的一次演讲为这一复兴奠定了基础。他说:“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公平、公正、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1)
数周后,中国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在一篇讲话中阐述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这就是“通过协调不同利益、整合不同观点、化解复杂矛盾来达成共识”。(12)
尽管“和谐社会”这种语言听起来像是理想主义的和虚无的乌托邦般的,尽管胡锦涛和温家宝一制强调“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是公平、公正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并承担其成本,但这一提法的政治含义仍是极为威权的。在中共领导人看来,为争夺社会经济利益展开的未经协调、混乱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和谐;由于不和谐会导致不稳定,因此就需要一种凌驾纷争之上的有凝聚力仁慈力量,在冲突的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有权威的、综合的共识。因此,“和谐社会”的说法预示着存在一个——姑且可以称为“明君”的——能够忠实反映、代表、调解所有“合法”层面社会利益且镇压顽固不和谐势力的家长制的、高高在上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并无二致。
协商式列宁主义的未来
通过用家长制咨询替代自主性的政治参与、吸纳替代代表权、建言替代赋权、以及构建共识替代利益冲突,中共已经能够避免民主多元主义(democratic pluralism)公认的太多杂乱、太多混乱的情况。但亨廷顿所提出的制度势在必行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的党国是变得更为的高度制度化和更具有回应能力了吗?例如作为一个管理机构是更为有效率了吗?如果是这样,这有助于增加还是减少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可能性?
最近,由杨大利所提出的对于中国治理品质改善的乐观评估,聚焦于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一系列由中央政府采取的行政改革以及行政调整上(13)。在杨大利的著作《重构中国利维坦》(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一书中,杨列举了由中国高层领导人所做出的有效的“行政修补”方面的许多案例。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权力下放之后,已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税收额,一场影响广泛的的新税制改革在90年代推出,有效地恢复了中央政府的的财政权威。
再者,当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人浮于事,出现了失控的预算外支出,在县和乡镇层级事态严重到有出现失控局面之虞时,为了“扁平化”行政级别,减少地方政府的裁量权中央政府再次介入,通过相应的措施巩固了乡镇政府并取消了农业税。
当中国的主要银行在90年代末被不良贷款淹没的时候,中央政府同样以一系列的行政调整施以援手,消除了省级银行分行,把不良贷款转移到了资产管理公司,对主要银行进行了资产重组,使金融体系导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这些改革的有益效果已经广泛地显现出来了 。
当腐败的或非法的征地和房地产开发计划不断升高的发生率导致了近十年时间中广泛的农村抗议的时候,中央政府以同样的方式加强了对土地使用规定和使用权出让金管理的控制。
最后,当大众抗议开始针对地方政府无视环保法规和条例时,国家环保总局设立了区域监督中心,监测和监督政策执行情况,以之作为一种平衡力来地方政府片面的、经济增长导向的那种偏向。
杨大利的观点呈现为明显的乐观主义的关键,就是从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例子得出来的,就在于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习曲线,设计了有效的行政修补来处理突发性问题;并且因为那样他们成功缩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巨大鸿沟”,那种鸿沟曾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的一大特征。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已经大幅增加了,尽管中国还是非民主的政体。
但是这种观点也有人对其持批评态度。对中国近期的行政改革持批判性立场,裴敏欣在他的新书,《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一书中认为行政调整,虽然短期可以减轻某些类型的社会问题,但这种做法长远来看却是一条死路。
这是由于中共一手笼络新兴社会-经济精英的同时另一手则坚持使用强制性的政治管制去对处理异议这种主导策略所导致的,这种策略被裴敏欣称之为“非自由主义的调适”(“illiberal adaptation”),实际上已经提高了而不是减少,一个掠夺型的、“裙带资本主义的”精英以与一个无权力的,原子化的大众社会之间的紧张局势。其结果就是裴敏欣所谓的“陷入困境的转型”。
“在中国,对未成熟的市场力量进行指令和管制的做法使共产党从有限的改革中,提高了效率,以维持旧的指令性经济这一未经改造的核心成分——这是共产党在政治上 享有最高权威的经济基础所在。在一个“陷入困境的转型”中,统治精英对于真正的改革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可以誓言改革,但大多数这样的承诺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的抑或只是旨在维持现状的战术性调整而已。”
与杨大利不同,裴敏欣在后毛泽东时代预算权威权力下放以及地方政府掠夺兴起之间看到了一种明显的结构性联系。他指出,中央政府1993年给地方政府授予了广 泛的权威其能够筹集和保留预算外收入引发了毫无约束的财政掠夺和浪费,因为地方官员筹资和开支都免于受到任何密切监察或受到任何由上而来的监管的制衡。
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由结构引起的“道德风险”,不能单靠行政修补来克服,因为它建构到了缺乏水平政治问责制的有效机制的中国政经的基本结构中。(以委托-代理关系的语言来讲,本应提醒中央政府注意到地方层面严重问题的“火灾报警”机制已经无法起到作用,所以政权必须越来越依赖于“警察巡逻队”去监督和控制其地方代理人。)
行政调整无法去防止以及惩罚掠夺和腐败尤其严重的乡镇层级所做出的类似行为,在那里由于缺乏有效的地方监督和问责性机制,非法的财政收入汲取情况已经极其的糟糕。这种情况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农村抗税、抵制甚至是有组织的反抗发生率的急剧上升。
虽然村民选举被认为是有助于约束最糟糕的农村掠夺行为,但这并没有导致重大的“民主赋权”(“democratic empowerment”)给普通村民。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原因则有两个:第一,由于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和筛选工作是由地方党支部所做出的;第二,当选的村民委员会没有独立的政治和财政权威,而是完全服从于乡镇政府的代理部门。
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的决策也没有解决地方财政不平等的问题,因为由此产生的预算短缺的情况,打击的正是那些本已缺乏充足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品供应(包括负担得起的公立学校和卫生保健)的贫困农村地区。
因此,裴敏欣视行政调整为最终注定要失败的举措,因为它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在政治结构上的根源问题,而他的结论是:
“在一种全国性的改革精神,或富有远见的改革者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似乎走在了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长征道路上。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是在证明现行政策是有理的,但却否定了改变的必要性,使得那样的困境将长期存在下去。凭借这一势头,党可以得过且过一段时间,但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在没有大变动的中途纠偏情况下演变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14)
结论:中国往何处去?
鉴于杨大利和裴敏欣之间、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那究竟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的局势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这个国家政治上又会朝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中国的非民主式发展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随着时间流逝成为一个有效能的,新加坡式的“行政-主导的,管制式国家”(确实,这就是中国新领导层所钟意的模式)
但 是支撑在“新加坡模式”背后的是大量独一无二的经济、人口和制度因素,那些因素却都是中国所缺乏的,包括了:强劲的法治,一个专业的不腐化的公务员团队; 高人均收入以及教育水准;新加坡也不存在一个庞大的、贫困的农村人口(毕竟,新加坡仅仅是一个城市-国家,尽管是一个有着良好管理的国家)
此外,尽管其“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政治体制以及一党独大的局面依旧,但新加坡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选举竞争,一个多元的媒体以及发达的公共舆论机构,这些都是今日中国所完全缺乏的。例如,执政 党人民行动党(PAP)必须定期在公开选举中与其他政治势力展开竞争,因此政府必须密切注意公众的情绪。即使这种不完善,半吊子的反馈机制都是中国所缺乏 的,中国想要涌现为下一个新加坡只有着很小的机会。
最终,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和悲观之间的主要区别归结到了一个问题上,即中国现政权,我把它们定义为“协商式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当得到各种各样的由杨大利所描述的行政调整的援助之后,是否可以有效地以及长远来讲对中共党-国起到增加代表性、透明度以及问责性的作用?不用说,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只有着极少的共识存在。
我自己的看法,往往介于乐观和悲观两种态度之间。在相对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发现我大致上与亨廷顿意见一致,亨廷顿认为现代性的选择压力最终会倾向于民主发展,因为民主有着较优的能力去调适,协调,代表和回应新兴的社会力量和压力的多元性。
更为近期,亨廷顿似公式化的表述已经在Bruce 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 George W. Downs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发展与民主”(“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中 得到了实证性的证实,这篇文章2005年的时候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Bueno de Mesquita 和Downs所提供的实证性数据支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一个开明的,前瞻性的威权政权可以经由选择性的结合增长导向的经济自由化以及对待异议方面习惯性的 封杀“协调性事物”(包括了组织以及集会的自由、投票权以及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来延长其存活时间:
“但如今各色各样专制和非自由主义的政府(illiberal governments)至 少能长期推迟民主来临的实例比比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很多这样的政权经历了广泛的经济发展却并未发生相应的政治自由化。也有独裁者有时不得不引进 温和的政治变迁,却成功的限制了变迁的范围,从而保住大权不失。为什么从经济发展的肇始到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出现,往往会出现那么漫长的滞后呢?答案在于专制政府越来越老谋深算。虽然发展理论家们对人均收入增长会导致民众对权力要求的预想是 对的,但他们总是低估了那些压制性政府挫败这种要求的能力。独裁政府在避免经济增长的政治结果方面越来越长进了——以致如今经济增长非但不能减少它们的生 存机会,反倒实际上帮它们存活下去了。”
“不过从长期来看,由于经济增长提升了有效政治竞争者涌现出来的可能性,这将会威胁压制性政府的政治生存。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提高了给赢家的奖额,从而抬高了政治游戏的赌注,经济增长也导致有足够时间、教育和金钱去参与政治的人数上升。这两种变化都会启动一个渐渐积聚动力的民主化进程,最 终冲破独裁现状的羁绊,取而代之开创一个竞争性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局面。”(15)
Bueno de Mesquita与Downs分析了历史上150个案例的数据,归纳出透过把经济自由主义与紧抓协调性事物(“coordination goods”)揉合在一起,威权政权可以多延长它的预期寿命10%-15%,透过最长大约10 年时间,推迟了民主化(或是政治上崩溃)的爆发。如果现政权并不很快开始引入一系列的多元主义的反馈机制,并提供一个更大范围的“协调性事物”,那么长期 来看,再多“行政修补”或“经济自由主义”的做法也不可能有效地避开政治不稳定。
原文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ter 1 et passim.
6 Beijing Review 30:45 (November 9-15, 1987), pp. VI, XV.
8 Ibid.
相关阅读:
译者的“译者频道—深度分析”专题
译者“@Freeman7777”、“@jiangge09”、“@hsinwang1982”的个人专辑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看中国”索引。
©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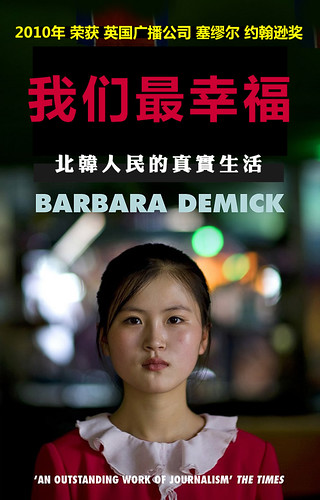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