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urray Scot Tanner(兰德公司资深中国问题专家)
原文刊载于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年夏季刊 pp. 137–156.
原文下载,http://www.ciaonet.org/olj/twq/sum2004/twq_sum2004h.pdf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在一家杰出的美国报纸2003年6月的一则电讯中描述了一件“少有的、只维持了很短时间的示威活动”,这是由100多位愤怒的上海公寓住户在抗议他们被强制拆迁、为奢侈的住宅让出地皮。这则经过严格研究的报道最为明显的错误之一是对这类抗议做出了“少有的”这种评价。根据来自中国警方自己所发布的新一波前所未有的国内治安数据,中国的公共抗议事件在数量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起,远比大多数外国分析家所承认的要远为来得庞大。近期大量的警方报告也指出公共抗议事件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在其规模上以及组织程度上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中国以及其他处于开发状态的社会不幸地没有为估定这种程度的抗议给中共掌握权力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威胁提供尺度,更不要提为肯定地预测一个“即将崩溃的”中国提供什么标准了.1社会动乱已经在北京当局负责国安问题的人士中激起了一次巨大的政策辩论。在他们内部的讨论中,中国公安系统的分析家以及官员们正在从根本上重新思索了一个变动社会发生大量动乱事件的来源以及对付它们的策略。中国警方中的许多人士正在坦承是经济、文化、政治变迁,而不是敌人阴谋,强化了这种使得秩序出现危机的势头的兴起。一些安全问题专家甚至小心地断言,除非中国进行严肃的制度变革,否则使用强制性措施以及保持快速经济增长都不足以遏制住这种动乱的势头。
作为胡锦涛领导下的新领导层,努力想要找到一个更为实际的以及老练的策略去掌控动乱并且在改革与社会控制之间达致一个有效的平衡,这些内部政策辩论将形成他们所获共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正如这些分析所强调的,努力去控制动乱会迫使北京当局的领导人去面对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以来比其他任何时刻风险都更为大的困境。以比较少暴力的警察战术所进行的实验,对示威者做经济上的让步,以及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宁的社会中进行更为根本的制度改革都冒了进一步鼓励抗议行为的风险。然而如果党要避免再次诉诸于1989年式的暴力行为或被迫参与到一个更为根本的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再次谈判这种终极的困境,那么这些挑战就必须找到正确方法来加以解决。
美国也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动乱并且体认到其潜在的对于美中双边关系的系统性影响。美国政府强调了北京当局所涌现出的具有自信以及国际合作的新型外交,通过不断升高的北京当局对于一系列涉及到战略以及经济议题风险的观察如此恐惧不稳定正在越来越限制以及复杂化双方关系。不可避免地,北京当局努力想去寻找到一个新的并且希望有更少压制性的策略去保证社会秩序时,它会面对重要的社会控制危机。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现在开始草拟对策反应,那将鼓励北京当局去加速其制度改革而不是转变为1989年那种暴力措施。
抗议不断增加
由中国警方领导层,公安部新近发布的内部统计,证实了公共抗议活动呈现出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官方把那样的事件称为“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有着形形色色的形式,从和平的小规模群体上访和静坐,到游行到集会,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示威,民族骚乱乃至武装冲突以及暴动。2
官方提供的社会动乱增长的比例真的是很令人感到震惊的。警方承认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增长了268%(从8700起增长到了32000起)。在这段时期中,没有哪个单一年份的社会动乱的增长幅度是低于9%的。根据中国警方在香港新闻发布会上所引用的资料,在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和1998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尖锐的25%和67%,并在1999年又增长了28%。在2000年1月到9月中国目睹了超过30000起的群体性事件,按照相同比例推算该年度估计要发生40000起群体性事件,比1999年增加25%。3
尽管没有办法获得2000年之后全年度的数据,但所有证据都显示中国的社会动乱仍在今天保持在高位上,虽然不清楚总的数字是否仍在继续增加,或是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这样的数字是否就会开始减少,或是当规模增加的时候,发生的频率则会逐步下降。在任何情况中暴露出的问题都清楚地表明事态依然是严峻的,在2001年4月,由中共组织部所广泛公布的研究归纳出群体性事件仍然处于增长状态,尽管它并没有提供统计资料。中国中部省份的警方报告说在1999-2001年期间,增长率为40%,在另一个中部省份,地方当局宣称与1999年同期相比的话,增长了35%。在2002年春天,尽管关注集中在发生于东北工业城市的辽阳和大庆的大型、长期的工人示威活动,不堪其扰的朱镕基还是告诉来访者说他的办公室被数百件关于劳工骚乱的报告给淹没了。最后,2003年9月末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宣称了抗议活动的多种形式,包括有“集体上访以及阻塞道路以及建筑物”,正在全国范围继续增加。4这样的增长已经广泛的遍布全中国,尽管增长至的水准以及比率,每一省都差别很大。
明显的是,中国没有其他地区比老化的东北工业地区遭遇到的阻碍更甚。在那里,自由市场改革已经严重损害到了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在90年代中期的好几年中,甚至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吉林省的警察每年都遭遇到了平均5000起以上“涉及大规模人数参与的群体性事件”——那样的事件至少涉及到了50名的抗议者。然而这些数字拿来与发生在辽宁的数字进行比较的时候,就显得很苍白了。在辽宁省,抗议活动已经自90年代中期以来爆炸性的增长起来了。该省的公安主管宣称在2000年1月到2002年9月之间有令人震惊的9559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平均下来每个月发生290起,或是在差不多3年时间中每天发生10起。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据报道这些数字与1999年的报告相比的话,居然还代表了一种局部下降的趋势。5
不断变换的抗议方式
对那些关注中国内部稳定的人来说,抗议活动的原始数字远没有其在规模上(组织化水准上、要求的激烈或暴力的程度上)急速上涨来的重要。中共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使其大大避免了其在欧洲的列宁主义同志所遭遇到的命运,这多亏了它不仅在防止大规模、良好组织过的、有着广泛反政权诉求发生上,还镇压了可以动员起这些抗议活动的有组织的反对派或公民社会团体上的能耐。已经吸收了天安门示威活动的残酷教训,在9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中国的抗议者自我意识到要约束他们的行动。大多数不满的公民婉拒去建立可能威胁到党的能够长期维持的地下组织。他们的抗议活动很少包含有各色人等,通常都来自于同样的工作单位或村庄。抗议手法则保持在审慎的和平状态,并且诉求集中于具体的地方议题而不是广泛的体制变动上。确实,为了避免官方的怒火,许多上访者挨着痛苦去再次确认其对党中央领导层的肯定,声称他们只想要地方领导人遵守北京当局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而已。政治科学家欧博文(Kevin J. O'Brien)已经富有创见的为这类的抗议活动取名为“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指出这类抗议活动不仅只对中共当局造成了些许威胁还给北京当局提供了机会去形容自己为被不守法的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员造成困扰的公民的救世主。6
然而近期的报告指出,尽管大多数抗议者的要求仍然是有局限的和具体的,但社会动乱在许多其他方式上开始放弃自我设限的依法抗争模式。最为明显的信号是由安全官员所提交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了一个朝向越来越大型示威活动发展的清晰趋势。有许多示威活动涉及到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或甚至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7在2002-2003年间,发生于辽阳以及大庆市的数千工人罢工以及发生在安徽的学生示威活动都凸显了这个趋势。尽管公安部声称在1999年间全国范围的警力只处理了125起涉及到1000人以上的的抗议活动,但省级警方公布的报告却清楚说明以上数字极大的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例如,在同一年,西南省份贵州省单独报告说发生了21起涉及到1000人以上的抗议事件——是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尽管贵州统计出的抗议活动总数只占到全国范围32000起抗议活动次数的不到1%。沿海省份福建省报告说2001年上半年抗议活动的次数不高于2000年同期水平,但涉及到的抗议人数却已经增加了53%。8然而,辽宁的问题再次使得其他省份所遭遇的问题相形见拙,据警方估计超过863000名公民参加到了9000多起发生于2000年至2002年之间的抗议活动当中——平均下来每起事件有超过90人参加。与前些年相比的话在平均规模上出现了超过10倍的增长。不可避免的是,这类事件的真实规模极大地增加了他们会超出(当局)控制的风险,而不管抗议领头人想要约束诉求以及参与手段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中国警方以及外国观察家也意见一致地认为抗议者的组织水平在逐渐提升当中。尽管下决心去努力削弱组织纽带,警方报告还是说他们所面对的许多抗议者——在某些地方确实是大部分人——现在正以形成组织为荣,由指定的领袖,“公共发言人”,“活动人士”以及“地下核心集团”来完成这种组织化工作。9为了回避反对“非法组织”的严酷的法律,许多这样的团体据报道都挂靠在合法登记过的产业协会里,例如:官方工会、家庭以及宗族组织(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并且主要是非政治的社会、娱乐性甚至是体育性团体上。一位沮丧的官员抱怨说地方抗议者现在“已经出现了为了上访活动进行集资、聘请律师以及邀请新闻报道者到抗议事件中来的迹象”。10
示威人士正在越来越多的克服中国所实行的共产主义为约束异议而进行的标志性手段之一:由自我约束的,细胞化的邻居以及工作单位所组成的巨大网络。在历史上,通过只允许让对其他单位抗议怀有潜在同情的工人与农民保持很少的经常性联系,这些单位既被动又主动地控制了动乱活动。由于遭受到这种限制历史上抗议者主要集中于针对地方官员并且他们的诉求保持在可掌控的狭窄范围里。负责安全的官员为了防止更广泛的组织化透过严酷的惩罚与其他单位取得联系的那种努力增强了这方面的障碍,视这些举动为对中共统治怀有敌意的初步证据。在与外国人对话之中,不满的工人以及农民频繁的测试着这种划分和统治制度的成功之处,强调了他们小心的努力以避免在联系方面被当局抓到什么把柄。11尽管如此,许多近期的警方报告仍然一致认为联络在近些年中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12安徽省的警方报告说11家地方建筑集团联合加入到组织了2002年1月份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中,该抗议活动阻塞了省会城市通往政府办公室的道路。13
中国的抗议人士也在证明他们是敏锐的学习者,他们展示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计谋上的以及技术上的老练。手机、短信以及互联网、电子邮件使更为快速以及更为灵活的组织化变得可能。警方抱怨抗议人士现在出现的更为突然,在有着距离的地方所发生的同时进行的、协调性的行动,急剧地使警方做出充分反应的能力负担了过重的压力。抗议人士展示了一种强烈的支配政治性街道剧场的能力,抗议领头人现在惯例性的把老年居民、妇女以及儿童放置于示威活动的最前线,以此羞辱他们所抗议的对象并且麻痹警方。警方面对这种伎俩所显露出的沮丧是一目了然的。近期由武警两名官员所提到的发生在新疆的穆斯林抗议活动的报告可以佐证此点观察.以熟练的委婉式说法,他们抱怨说,“因为骚乱者混杂在许多少数民族妇女以及儿童中,公安以及武警的力量无法采取适当的措施去处理抗议活动”。14
最后,尽管中国警方坚持说绝大多数抗议活动仍然保持了和平状态,但暴力的抵抗清楚的显示正处在一个上升的势头。例如,在1999年,贵州警方报告说涉及对党和国家官员的肢体攻击的抗议活动增长了42%,导致了17死,282伤。这种增长部分反映了暴力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显著增长。死于工作岗位的警察在1949年至1978年间平均每年处在一个令人吃惊的36人的低位水平上,现在则已经暴涨至每年450-500名,数倍于美国警察的死亡数字。要知道美国可是一个拥有更沉重武器压力的社会。尽管大多数警察因工死亡是交通事故以及以及不明智的与拥有更好武器装备的犯罪分子进行搏斗的结果,但有证据显示,抗议人士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暴力对镇压行动做出反制措施。
重新评估抗议肇因
面对抗议活动的快速增长,顶尖的中国负责内部安全的专家们以及警界人士正在重新评估隐藏在社会动乱之后的导致其发生的那些因素以及能对付它们的策略,对于天安门示威之后所实施的官方教训他们所持看法分歧明显。更为具体来讲,许多人现在相当不强调陈腐的阴谋论看法,那种看法主要把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归罪到中共的外国以及国内的敌人头上,这类看法反映了经典的列宁主义坚持声称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里,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不是单纯的,它肯定是被鼓动之后才产生出来的。(幕后有黑手在操控社会动乱事件)
在发生天安门示威活动之后的那些日子里,这种列宁主义的阴谋论世界观由顾林方,中国负责“政治安全”的公安部副部长所发布的一篇关于抗议事件的报告得到了典型的印证。15为了记录发生在1989年的那一场阴谋,顾林方列举了成打的据称在抗议领头人以及具有改革思维的共产党官员,外国学术机构以及,当然咯,西方国家的以及台湾的情报机关之间的不法接触。这位副部长极力责备党内改革者为处心积虑的引发叛乱的阴谋家。列宁主义的思想深入到了他的骨髓里,顾拒绝接受任何社会学家已经知道了几十年的事实,即无论哪个社会,成长与变迁速度如中国一般时,政治上的抗议活动有所增加,是一种普遍会发生的情形。
然而,直到1990年代末期的时候,来自公安部自身智库以及大学的许多分析人士认识到之后进行的威慑社会动乱发生或把它限制在一个非常低水平上的努力正在遭遇失败。他们已经以一种未曾料想得坦诚的学术成果来对这种现实加以回应,他们对于官方针对1989年在抗议来源以及处理它的最佳策略上进行了重新考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新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有局限的。通过重新评估官方指控天安门示威活动是一场“反革命叛乱”,没有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敢于公开质疑一党统治或真切面对这一历史上的复杂而又麻烦的问题(a historical can of worms)。然而,在对社会动乱所做的新分析中,对于社会科学的信赖越来越取代了偏执性见解。
尽管分析家们怀疑是“敌人怂恿,抗议活动才发生的”这一看法的程度在今天仍然有着广泛的差别,但越来越难发现接近于顾的那种对阴谋的偏执看法(主要的例外是很可能过度的归咎于FLG和穆斯林分裂主义组织)。即便相对传统的分析家也只好把“国际敌对势力”当成是动乱许多来源中的一项而已。大多数可以获得的政策分析现在主要把动乱责怪在近似于西方学者援用到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力量的列表之中。间接的把敌对势力这一要素归为第二重要的分类中。例如,一个省级的警方副主要负责人更是率直的淡化他所在区域里的“敌对势力”,反而提到“我省目前只有很少萌芽或趋势显示出有这方面的迹象,但我们绝不允许自己忽视他们。”
这种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上的后果是大多数分析家现在都宣称绝大多数抗议活动导源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来源于“敌我”之间的冲突。一份准备于2000年的公安部内部的文件,据报道使这种对于抗议事件的指控成了官方的口径。17根据国内的安全策略,这种区分典型地,尽管不总是这样,减少了对于强制手段的依赖。回应这种判断的是,自1999年以来公安部及其智囊已经采取了新的形容抗议活动的标准词汇“群体性事件”(“mass group incidents”),这个术语假设抗议者是“大众”(“the masses”),暗示了强力的同情性质的弦外之音。
新的公认看法:是经济,傻瓜!
取代阴谋理论,大多数安全问题分析家现在都支持以典型的经济原因来解释动乱问题的看法。一些人声称经济上的冲突最终强化了所有社会动乱。像大多数西方分析家那样,中国分析家强调了北京当局进行了20年的、充满痛苦的对其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包括下岗、失业、不正当的扣押工资,以及住房津贴、健康保险费用以及退休金。警方专家承认所有中型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50%-80%现在都处于严重的财务方面的困难之中,这样的情势到2001年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了2700万工人的工作。18
数量上超出人意料之外的公安系统的分析家们显示了对相当多工人以及农民抗议活动(这是警方原本理应要去镇压的)毫无遮掩的同情。在他们的行文中,他们把下岗人士示威者形容为“被剥削的”、“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人士”、“受害者”、“经济竞争中的输家”,是由社会不公以及自由市场的“没有同情心”才驱使他们去进行示威的。他们坦率承认许多抗议者都是通过非法交易或带着公司资产潜逃在外的不法的管理者、那些使他们的工厂走向破产的人的受害者。一位上海的分析人士近期声称55%的抗议活动要归因于企业经理所进行的非法活动。19
许多警方专家都对中国越来越高的不平等收入分配持有一种特殊的厌恶。他们几乎是以幽默的方式提到,即便是在市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25年之后,中国的警察力量仍充斥着“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Communist sympathizers”)。一些人引用比较发展研究的成果声称这样广泛的不平等把中国置于了一个不稳定的“真正危险的地带”中。以赤裸裸的批评主义(judgmentalism)的方式,一份省级警方报告认为不平等加剧了动乱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民意识到了中国新富阶层中的许多人是通过腐败、不法企业获得了“爆炸性利润”才获得到财富的。
北京当局希望在社会动乱威胁到政权存活前能走出它的阴影,就像前任总理朱镕基在2003年3月的告别演说中说的那样,“发展是基本原则,是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全国经济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朱镕基也认为改革的步伐不得不加以平衡以防动乱的风险。20
然而即便是公安部专家的数据也暗示北京当局如果它相信单独的经济增长就会使动乱处于可控状态,那样想的话他们就可能是在做自我欺骗。抗议事件在1997-1998年间的快速爆发暗示了社会动乱可能与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越来越高的事业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抗议事件根本上的持续性增加,起码是与长期不间断的经济变迁,诸如越来越高的不平等是符合的。尽管不断趋缓的经济增长以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数据证明了动乱开始越来越快速地增长在时间点上是不晚于1993-1995年才起步的。当经济增长率突破10个百分点时,抗议事件也显示了一种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维持在相当高的数字上(并且至少在一些省份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即使当经济增长率复苏之时(请见图1)。
更有甚者,反观自1993-2000年来的数据,动乱事件也在1986至1988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火爆增长,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以及腐败在学生以及工人之中引发出了大量不满情绪。因此,自1986年以来,在通货膨胀性高速增长,衰退以及复苏期间社会动乱已经在同时上升了——这对任何简单的针对社会动乱所做的经济决定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一些警方分析家明显地认识到了这些缺失,他们承认社会以及政治力量也正在引发社会动乱并且这种情形会继续下去而不论经济的景况如何。
更为具体的是,许多分析家把越来越多的动乱归因于中国在政治、文化上面的深刻变迁。本个世纪的渐进的、进步的政治改革正在形成他们所归纳为的一种新文化。那是更为积极地、更为开放、自信而大胆,甚至是“发达的”。中国的公民现在只是不大愿意去容忍不公、腐败的官僚,这些人更为愿意把它们的抱怨诉诸街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当时,邓小平在社会盘算中吸取到了一个残忍的教训:街头抗议所冒的风险、所带来的危险远超过任何潜在的回报。然而15年之后,许多警察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逻辑占据了上风,不满的公民越来越信服平和的抗议活动明显不太危险并且不仅有效而且通常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赢得让步的一种方式。警方消息来源正在习惯性地引述一句流行的口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制度的失败
最为深刻的新的警方批评认为群体性抗议某种程度来讲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一项产物。但是在政治和司法体制没有跟得上变化之时得到了加剧。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引发了大众在经济和政治需求上的快速膨胀。当公民还没有学会通过可行的政治和司法渠道去了解该如何去发出诉求时,或是如果这些渠道被堵住好或欠缺发展时,沮丧情绪就不可避免的会满溢到街头去。21社会经济的变迁可能会生成这些不断强化的诉求以及社会利益的冲突,但通常是政府缺陷导致这些矛盾转向了敌对性的以及危险性。
尽管在这种分析背后以及表达这种分析时所使用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常常表现出它反映了1950年代中期毛式思维的一种温和阶段的形式。许多西方学者立即会认识到这种关于动乱的理论是亨廷顿1968年时写作的经典《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许多中国警方分析家间接的宣称其观点收到了亨廷顿的影响。一个这样的分析家认为这中国越来越多的动乱导源于“不完美的政治结构”,它提供了不充分的途径让人发出声音,安抚以及平衡大众诉求的激增。缺乏“合适的渠道”去说出他们的要求,公民通常经由“不合适的渠道”去发表他们的诉求……诸如非法集会、游行以及示威。22
这些分析家认为中共以及国家无法冀图去遏制社会动乱除非他们致力于解决制度上的动乱问题催化剂,包括政府错误处理社会紧张以及腐败的、无同情心或滥权官僚。23以令人吃惊的严厉口吻,一些警方官员以及分析家严厉斥责地方官员以及他们那些身为执法者的同事,因为他们的偏袒,腐败,以及倾向于从手无寸铁的农民和工人那里缴收非法罚款。他们也谴责了中国糟糕的不健全的司法制度无法去从中国那西部拓荒式资本主义(Wild West–style capitalism)进行剥削的企业拥有者那里对失业者和弱势者以及非法转移了工人的养老金和保险基金的钱进行保护。他们强调,任何控制中国社会动乱的成功策略并不应该依靠由国家执法机关所进行的镇压,不管他们会表现得多么职业化以及有效率。除非是与更为广泛的司法以及民主改革混合在一起使用,那才会激励国家对大众的诉求做出更有效的回应,不这样做的话,抗议活动不可能被成功地解决。然而,警方分析家以及官员在私底下向党的高层推荐了什么具体的政治改革建言仍然是一个引人探寻的神秘之物。当然咯,在中国严厉的一党体制中,还没有人敢于公开的提及亨廷顿自己所倾心的那种制度性解决方法:一个具有竞争性的两党体制可以和平的整合新团体以及诉求进入到政治中去。
处于变动状态的安全策略的两难处境:从威慑到遏制
不管他们偏好于以何种解释来说明抗议事件的兴起,所有中国警方分析家都接受了亨廷顿的一项间接的观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力量的一个关键任务是通过遏制抗议事件以及在它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前使压倒性的国家统治能力能压制住大众的诉求。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的没几年时间,为完成这项目标的中国警方的策略集中于想要威慑或快速地以压倒性的力量镇压示威活动。然而,当警方的安全策略威慑以及快速镇压转到一个更具放纵意味的遏制与掌控的策略上时,他们正在面对比以往更需谨慎对待的困境。负责安全问题的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主要目标是威慑抗议者,暴力的伎俩是可以帮得上忙的。然而,他们现在正越来越承认温和水平的抗议事件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抗议者得到公众(确实是这样,甚至连警方人士也被包括在内)的相当多同情。一旦一次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如果他们诉诸于残忍的、笨手笨脚的暴力警方就要冒着进一步激怒抗议者的风险。结果是,在警方战略家中先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关注最近已经从如何最佳的威慑住所有抗议活动转移到了如何避免错误使用武力以及如何避免偶然地加剧大众的愤怒上了。
今日安全力量的新目标是要通过更多温和的、职业化的警力去对付抗议活动以及去限制警方使用暴力强制手段去对待即将到来的聚众暴力、纵火、抢劫或对关键的政府建筑进行攻击的事故。当然,这种做法,言下之意暗示警方将让许多低调的非法示威继续,而他们则将继续设法维持现场秩序。警方领导人越来越不鼓励官员们陷入到人群中或制造大规模的逮捕,并且敦促他们不如去维持遏制,去仔细收集情报,并等到人群已经分散之后才开始拘留抗议活动的领头人。处理了先前提及的辽阳工厂工人抗议的警察就有技巧的采用了许多这类型的招数。24一些警方分析家甚至更进一步,提倡警方应该充当中间人,调解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向示威者让步。虽然这种温和的遏制手段最小化了任何抗议都将恶化为暴力行为的风险,但经由发给普通公民信息,即现在参加示威将是较不具有风险和危险的事情,他们也冒着鼓励了其他抗议的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当局给地方警察在处理抗议活动上的指示通常是含糊其辞的或是有内在矛盾的,这就给了地方对这些指示进行自我解读或地方上犯错留下了大量的空间。结果是,许多警方有相当理由害怕这种对待社会动乱战术上的变动会使他们陷入麻痹、危险处境之中,陷入到愤怒的抗议者以及顽固的、要求警方坚决地重建秩序的地方当权者之间这种两难处境上。在这些含糊其辞的、矛盾的规矩中,能举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警察在使用武力上的原则,他们把这种原则命名为“三个小心”和“三项恐惧”。警方被指示要小心地使用警力、武器以及强制性措施,但北京当局也坚持说小心地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一点都不去使用它们。因此,中央的执政当局也指示警察去克服他们的“三项恐惧”,恐惧他们会为搞糟的操作承担责任,恐惧群众会包围以及攻击他们,恐惧事后警方既会在事后遭到官方的惩罚又会遭受到大众的报复。这些原则为地方警察试图避免要么惩罚得太过于严厉要么处理得太过软弱提供了很少的具体指导。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充斥着由地方官员造成的灾难,只因他们想要徒劳无功地去平衡这类矛盾性的指令。
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所偏爱的反抗议的计谋是去以一次性对抗议者被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支付一部分款项来进行收买——这种做法为警方创造出了巨大的难题。一些警方人士支持这种支付动作并且视这种作为是地方官员努力去为愤怒的、无论如何理应得到这些钱的公民解决真正问题的方式。当然了,这些收买做法,也让警方无法去执行不受欢迎的镇压动作。一个警方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的某些类型的工人抗议在官员们加强了健保以及退休金保障之后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其他的警方官员则拒绝这种被他们视为短视的、适得其反的甚至是危险性的做法。尽管收买可以有助于地方官员防止北京当局尴尬的发现其管辖范围内的本地抗议事件,但这种招数也创造出了一种危险性的激励结构(incentive structure)并且通过向公民展示他们也可以经由把他们的抱怨带到街头赢得让步冒了使抗议行为蔓延到其他区域的风险
领导层的回应
不幸的是,尽管这些警方针对动乱所作的辩论致力于要去解决显著的新议题,但许多重要的、吸引人的问题仍然是有待回答的。例如,我们不知道,在公安系统内部这些更为老道的对于动乱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它们的策略广泛散布到了怎样的程度,尤其是在顶尖的警方领导人以及警力中的基层成员中。如果暴力机关内部对于工人抗议者的同情变得强劲以及广泛时,在遭遇到抗议者时,它可能会严重的削弱警方的执行能力以及纪律。例如,有着很强的证据表明,在允许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示威并使其发展至超出控制的局势中,警方的同情在其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5分析也对中国的治安服务,尽管他们关注于社会秩序问题,是否在抵制政治改革上真的是一个团结的集团有疑议。一如以往,关键的未知问题仍然是:北京当局负责安全问题的精英私下场合给党的最高领导人什么建议,以及那样的思维如何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改革以及国内的安全策略?
自2002年12月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以来,胡锦涛还没有详细制定出针对改革以及内部安全的清晰策略来。胡是否和他的前任一样,也希望中共可以走出社会动乱的阴影,并且通过结合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收买、更为粗暴但也更为职业化的警力这些伎俩来规避不易进行的制度改革?抑或,胡会坚决执行显著的、会提供给未来的抗议者更好的司法渠道去发出异议声音的政治改革?这两种证据都有着相应的证据在加以佐证。胡经常公开坚持邓小平、江泽民所支持的顽固派名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他偶尔也隐晦的在处理大众紧张局势时呼吁“新思维”。26在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爆发期间,胡机灵地提倡更加开放的信息流动和政策讨论的做法。在2003年10月份,他也在未作具体说明的“司法结构改革”、“乡村选举”以及其他司法和近似于民主改革可能进一步为不满的公民发表他们看法打开制度性渠道方面号召做出“主动的”但“稳健的”进展来。27
尽管在同时还没有详细制定任何全面的针对国内安全问题的策略,胡正在给不满的公民发送具有相同危险性的混杂信号,一如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样:组织抗议仍然是一件具有极端风险的事情,但是抗议活动自身也经常因为抗议对象的让步获得回报。例如在2003年5月,组织抗议活动的数位工人被宣判了长期的刑期。另一方面,在回应发生于2003年冬天由数千安徽学生所发起的抗议活动时,据报道,胡命令地方官员满足了他们的一项要求,严厉的惩罚了杀害一名学生的汽车司机。
尽管有着一个令人期待的开头,他仍身处一个满是江的前同伙的政治局中,距离巩固其领导地位非常遥远,江仍然作为中共的中央军委主席潜伏在他的身后。江仍然有多大的权利以及多久他才可能让胡对中共自天安门示威事件以来一直所支持的针对动乱问题的具有高度风险的策略进行修正仍是不明朗的。然而从胡的角度来看,这种暧昧的继承制仍似乎使人怪异地联想起1980年代,当邓小平两次怒气冲冲地从退休状态中走到幕前开除了他感觉在对付学生抗议上太过于软弱的继承人。胡当然可以通过抓一些亲民性质的改革议题,正如他在对待SARS事件时所采取的公开信息的做法来加强他的公共合法性。但即使胡的最为温和的呼吁体制改革的做法也在激化谣言,说胡与更为强硬派的江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正如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的事件那样,这种对于领导层分歧的观察可以危险地给予一些抗议者勇气去认为他们在政治局中拥有一个亲密的盟友。对相对小心的胡来说,即便在群体性抗议事件发生之前表现出宽容或退让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高风险的策略。
不管领导层内部是否在处理动乱问题上是否有着真正的分歧,他们所拥有的选项可能是越来越狭窄的。正如那些警方辩论所显示的那样,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正在认识到威慑以及妖魔化抗议运动的老策略正在失败,低到中等激烈程度的抗议事件正成为中国的政治议价游戏中越来越常见的一部分。28治安力量中的许多人正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全新的强调遏制以及掌控的安全阀式策略(这种新策略集中于防止大规模有组织的反对派或暴力出现并且保护对政权存活至关紧要的那些重点城市以及机构)去对新形势加以回应。
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期间台湾、印尼、菲律宾、南非,尤其是南韩压制性政权的垮台指出了这种安全阀式遏制策略既不是稳定的又不是可持久的。当政权不再能防止慢性的、低激烈程度的示威活动,社会动乱经常不断地成为能保护政权的一个安全阀。相反,抗议的逐步增加直到政权必须要么通过极端的镇压再次确认其支配地位,要么与社会在更为基本的权利、政策以及制度变动议题上进入一个持续的重新谈判的状态。最终,看起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再次被迫去直面尴尬的选择,试着去再次学到天安门事件所获得的教训或与社会进入到这样的谈判中。尽管对于体制改革所进行的警方辩论可能暗示北京当局的一些负责安全事务的专家在那样的问题上有了自己的思考。但不可能有办法知晓当面对一个真正的、类似89事件的社会秩序危机时他们会如何做出反应,尤其是中共领导层会再一次团结在镇压另一次想象中的阴谋用暴力来镇压是必须的这样一种主张的决策后面。
社会动乱与新外交的局限
总的来说,中国负责内部安全的官员现在正以越来越坦率的态度认识到在他们社会中动乱事件的爆炸性增长——并不单单在于示威数量的增长,还在于他们的规模,影响到的社会范围,组织方面老练的程度,以及偶尔会发生的暴力程度。警方专家以及官员越来越从狭隘的列宁主义解释法中走出来并且承认大多数抗议反应出的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阴谋(这是官方对于天安门事件的说辞)而是一个对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真正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的大型地合法的群众反应。
然而通过承认动乱的重要性以及引发它发生的许多真正的肇因,中国的负责安全问题的领导人已经给他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当他们寻求更老道的策略去遏制以及掌控抗议活动时,他们再也无法完全去防止其发生。他们也迫使北京当局去更为公开地承认一系列数量巨大的政策议题——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因为中国激增的社会秩序危机而受到波及。
由于中国急剧增加的动乱的干系并不局限于中国,美国及其盟友也会从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动乱的态势而获益,尤其是其在美中关系上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例如,就像许多西方的分析家已经正确观察到的那样,在过去数年中,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外交政策,其标志是更多的国际行动,自信以及接触,尤其是选择性的参加多边经济以及安全机构。29与此同时,中国表现出无所不在的对于动乱的恐惧,就像是只有少数明显症状的一种系统疾病那样,已经静悄悄地潜入到中国的主要的双边以及多边关系几乎每个议题去了,这会为中国以其全新的外交做法走多远设下限制。不像中国的那些负责内部完全的他们的那些同事,中国外交领域的参与对话者不情愿的承认抗议事件越来越多的潜在影响到北京当局的外交关系,这很可能是因为害怕表现出承认它们政府的合法性可能会越来越遭遇挑战。然而,因为动乱继续在升高重要改革以及让步的风险,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为深重,并且中美之间近期的良好感觉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
例如,对社会动乱做经济层面的解释当前在北京当局中占据支配性的影响。社会稳定以及政权存活系于中共履行经济增长以及就业机会增加方面的能力。这种承诺强加了不对等性到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谈判上面。那意味着,华盛顿当局可以考虑的许多经济议题不仅仅是精明的讨价还价,那些经济议题北京当局还视其为与社会稳定或甚至是政权存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北京当局的关注就导致了其视处理诸如自由化人民币汇率或执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步伐这类议题具有一种足以致命的严重性,认为那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受到高度保护的国企失业方面的增加,尤其是在越来越不稳定的东北地区。与其通过执行系统性的改革在社会控制上冒进一步损失的风险,反而中国可以被期待的是提供快速的修补以及摆出表面上的姿态,诸如近期所答应的采购大量美国飞机以及其他出口屋子,始于90年代晚期,甚至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公安系统的研究者开始出版发行数以百计的对于通过WTO相关的改革可能会最严重冲击到的产业以及地区对于国内安全所会产生的可能后果。从西方国家贸易谈判者的立场来看,公安部的结论会构成一个真正的在中国最可能绊倒的WTO执行议题上的指导书。西方的商业官员会从这些公安部的研究的详细分析中获得收益。
类似地,比其它任何因素都更重要的是,害怕失业以及国内不稳定解释了中国坚决地不愿意去直面该国的那些越来越无力偿付债务的国有银行,并对外国竞争者开放金融部门。为了保持运作,国有企业正在依靠国有银行的贷款为生。当北京当局谈判进一步的开放其金融部门给外国竞争者的时候,领导层知道,通过允许给其公民更多的选择以使其存款都能进入到国有银行里,它正冒着消耗掉人力资源的风险,既统一资助这些贷款又资助了工厂工人的数百万工作职位。
恐惧动乱也使中国的全盘战略复杂化了并且加入了经济上的关系,吉林省以及其它毗邻北韩边界的地区抗议活动的大幅度加剧,最终意味着华盛顿当局以及北京当局在六方会谈讨论北韩核项目时有着各自偏好的结局以及手段会分道扬镳。这些日子北京当局和平壤当局之间没有失去多少爱意,并且美国以及中国清楚地对于谈判有着一种强烈愿望想要产生一个无核化的北韩,许多美国官员可能偏好更为强制的手段并且最终希望北韩产生政权更迭,然而北京当局会恐惧北韩的崩溃而释出庞大的难民潮涌入到中国最为动荡的地区。北京当局的一些资深的军事分析家已经公开地认为,部分原因是害怕在东北地区出现动乱,中国会暗示地把和平与稳定排列在朝鲜半岛去核化议题之前。30这些景象甚至复杂化了北京当局利用粮食和燃料作为杠杆的意愿,因为中国必须权衡给平壤当局所施加的压力以防止其加速崩溃的风险。美国和中国越被卷入到与北韩的谈判,中国恐惧社会动乱的想法就越可能加深华盛顿当局以及北京当局各自偏好上的差异。
美国反对恐怖主义而发动的战争与北京当局努力镇压民族-宗教异议活动之间产生的联接把华盛顿当局置于了一个需要非常小心对待的处境上。作为少数旧的阴谋论理论仍然占据优势地位的残留地带,北京当局的官方分析坚持把对待恐怖主义,少数民族分裂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作为一回事来对待,拒绝接受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平和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者居住其疆界内。对美国来说,为获得北京当局在反恐上的合作而又不对其所做的对少数民族的镇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华盛顿当局必须大幅度提高它收集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团体的可靠信息并且不要害怕对于中国的对话者做出清楚的区分来。
对于社会动乱所给出的不同假设也对西方国家解读北京当局战略建设上产生了一种强力的影响。美国分析人士中心性的辩论之一就是关注当直面国际安全威胁或诉诸于一种中国版的发动起爪牙采取好斗的国内行为以凝聚其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中共政权是否感受到了国内的威胁是否使其更有可能变得更为小心。中国的现代史并没有揭示在有内部冲突的时候发动这类“转移注意的战争”(“diversionary wars”)的许多例子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倾向于独立可能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情境,因为北京当局关注动乱及其高度依靠民族主义者以维系其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肯定会使其对台北当局作出让步变成一件非常具风险性的事。
第二项辩论关注于治安负担的严重程度,社会动乱强加于中国的国安系统以及随后的潜在中国威胁的观察。在所有对于中国快速增加的防务开支的关注之中,只有少数分析家已经明确地试图估算可以被称作是“政治不稳定紧缩”的开支,那是在说,多大比例的资源中国投掷于国家安全(广义上的)以支持越来越多的负责国内安全的力量,收买不满的工人,使无力偿付债务的生产防卫用品的工厂脱离债海,或仅仅只是确保军队的忠诚。
当北京当局辩论在处理社会动乱以及寻求新策略集中于掌控抗议活动而不是去除威慑它们所遭遇到的两难处境时,中国的外交伙伴也必须对此局面要有所准备,发生在天安门的示威活动以及北京当局作出的暴力回应使西方国家加以戒备。美国及其同盟需要更为坦率以及更全面的讨论对于潜在的中共领导人所会遭遇到的系列危机,北京当局所会做出的回应方式,以及结果可能会怎样,从采取新的镇压到进行改革,从慢性的低水平的不稳定到国家合法性丧失,同时体认到在影响一个可能视其存在处于风险状态的政权上他们受限的能力何在,中国的外交伙伴也必须创造性思考鼓励北京当局去看到社会动乱会爆发失控只有平衡的制度改革,而不是强制手段以及对阴谋的指控才是其对付它的最佳回应。
Notes
1.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2. The nationwide data are from a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s (MPS) Guards Bureau published in a larger June 2001 collection of national and local reports on “mass incidents.” See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d., Quntixing Shijian Yanjiu Lunweiji (Collected research essays on mass incidents) (
3. Xiao Tangpiao, “Ershi yu lai Dalu Nongcun de Zhengzhi Wending Zhuangkuang,” Ershiyi Shiji (
4. Available at www.mps.gov.cn.
5. Li Wenxi, “Development Forges New Glory,”
6. Kevin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 no. 1 (October 1996): 31–
55. See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eds. Elizabeth Perry and Mark Selden (
7. Fu Yongkun, “Jiji Yufang, Tuoshan Chuzhi Quntixing Shijian, Quanli Weihu Shehui Wending” (Actively prevent and appropriately handle mass incidents, make full effort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Gongan Yanjiu (Policing studies), no. 12 (2001): 44–46; Gongan Yanjiu (Policing studies), no. 3 (2002): 12–13.
8. Fu, “Jiji Yufang,” pp. 44–46.
9.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pp. 94–95.
10. Ibid, p. 287.
11. See Lee,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12. Ibid., p. 287.
13. Gongan Yanjiu, no. 3 (2002): 12–13.
14. Zhao Jianxin and Sun Liwen, “Some Problems to Be Grasped in Handling Mass Incidents in Nationality and Religious Areas,”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p. 318 (emphasis added).
15. Gu Linfang, “Drawing on the Turmoil and Riot to Examine Class Struggle in Socialism’s Initial Stage,” Renmin Gongan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October 5, 1989, pp. 3–9. This article is concluded in the magazine’s subsequent issue.
16. Zhang Shengqian, Shehui Zhian Shijian Chuzhi (Handling social order incidents) (
17. See generally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18. Zhang, Shehui Zhian Shijian Chuzhi, pp. 32–34.
19. Zhang Min, Shanghai Gongan Gaoke Xueyuan Bao (
20. Zhu Rongji,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speech, March 5, 2003 (transcript in Xinhua, March 19, 2003).
21. Zhou Guangyang,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pp. 14–17.
22. Zhang, Shehui Zhian Shijian Chuzhi, pp. 24–36.
23. MPS Fourth Research Institute essays, p. 58.
24. Phillip P. Pan, “Three Chinese Workers: Jail, Betrayal and Fear,”
25. On police behavior in 1989, see Murray Scot Tanner, “The Institutional Lessons of Disaster: Reorganizing China’s People’s Armed Police After Tiananmen,”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ed. James Mulvenon (Washington, D.C.: RAND Corp., 2002), pp. 587–635; “Chinese Bureaucratic and Leadership Battles over Public Security, 1989–1990: Dissecting an Organizational Disaster,”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arch 1997. See also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
26. On Hu’s statements, see Murray Scot Tanner “Hu Jintao’s Success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eds.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aryanne Kivlehan (
M.E. Sharpe, 2002), pp. 45–65.
27. “Hu Jintao Stresses Building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t Politburo Study Session,” Global News Wire, September 30, 2003 (translation of Xinhua article).
28. For a superb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 manipulation of the threat of unrest, see William J. Hurst, “The Forgotten Player: Local State Strategies and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Contention” (n.d.).
29. Two of the best analyses of this trend are found in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8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22–35; David Shambaugh, “Commentary: China’s New Engagement with the Regio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9, 2004.
30. Xu Weidi, “Resolv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Crisis and Mov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Out of the Cold War,” Shijie Jingji yu Zhengzhi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September 14, 2003, pp. 5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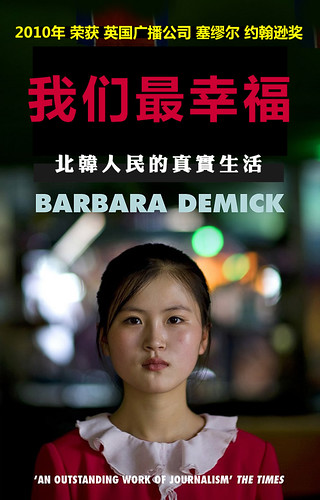


0 comments:
发表评论